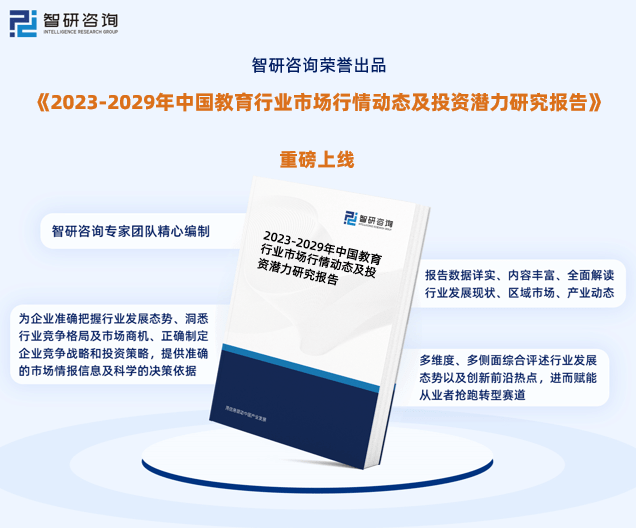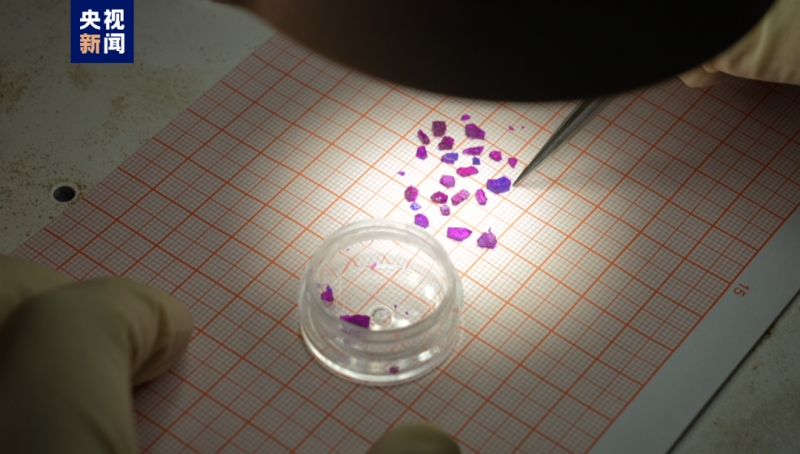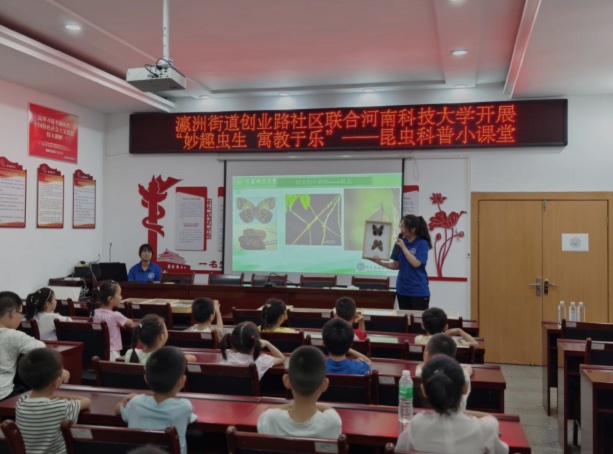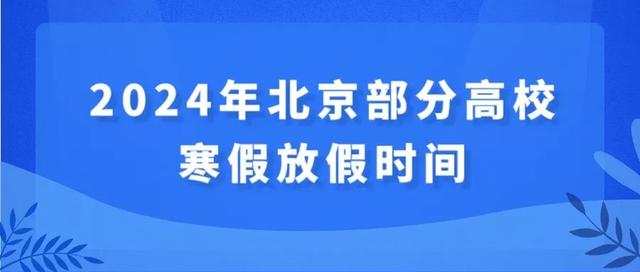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开篇就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由此引发了职教界的欢呼。
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开篇就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由此引发了职教界的欢呼。
事实上,职业教育“类型化”地位的确立并非新鲜之事,重要的是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国家认定。这一国家认定并非表明普职之间“同等重要的地位”已是现实的存在。长久以来,职业教育似乎总是“低人一等”,普职之间“同等重要的地位”是职业教育现实的、也是永恒的追求。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的观点自古就有,并形成了教育“二元论”。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是教育“二元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人的全部生活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鄙俗的,一类是高尚的。鄙俗的生活是以谋生为目的的劳作生活;高尚的生活是以深思为目的的闲暇生活。由此,他把教育也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培养人的理性和德性的“自由人教育”,即普通教育;一类是培养人的技艺的“非自由人教育”,即职业教育。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对职业教育持有明显的轻蔑态度。这种轻视职业教育的教育“二元论”思想一直流传在教育历史的长河之中。
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引发了政治、经济基础的变革,推动了教育民主思想的传播,自由教育只为少数人服务的观念受到冲击。正如美国永恒主义教育流派代表人物罗波特·赫钦斯所说:“如果自由教育是适合于自由公民的教育,如果全体公民又都是自由的,那么每个人都应该接受自由教育。”从而为自由教育面向人人提供了逻辑依据。自由教育的高贵成为人们普遍的向往,导致了对职业教育的冷落和社会人才结构的畸形。
十九世纪末,美国进步主义教育人物代表杜威倡导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思想,反对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对立,主张普职共生共存的教育“一元论”。“职业是文化之花,文化是职业之果”,杜威深刻地表达了两种教育共生共存、共存共融的辩证关系。美国的综合中学制度使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在同一所学校进行,正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思想的产物,这也引发了职业教育的深刻变革,对于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以史为鉴,凸显职业教育本质特性,建构职业教育的类型化体系,彰显职业教育育人价值,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是发展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知识类型的差异性是教育类型多样性存在的客观依据。普通教育是以传递陈述性、符号化知识为主的教育,内容主要是人文、科学知识;职业教育是以传递程序性、情境化知识为主的教育,内容主要是技术实践知识。以技术知识为教育的切入口,以培养学生技术操作能力、技术思维能力、技术伦理意识、技术审美情趣为个体成长性目标,以“职业准备”为社会发展性目标,以“产品制造”为实践平台,以职业活动为实践载体,实现学生“技术领域”的完整性成长,以及“公共领域”的整体性发展。进而,促成职业教育肩负起“推动社会改造”之历史责任。这正是凸显职业教育类型特征,促进职业教育优质发展,促成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实践逻辑。
“产品制造”是集理论与实践于一体的核心枢纽,是技能与学术的完美结合,是科技力量的功能性再现,是人类智慧的主体性表达。然而,在现实的职业教育中,由于“制造边界”在教学设计中过于窄化,造成学生技能培养与德性培育分裂、动作技能与智慧技能割裂、技术问题与技术过程断裂。进而导致职业教育学术含量下降,教学形态不够灵动,教学价值的完整性损失,职业教育“类型化”方向的迷失。
基于“产品制造”,改变职业教育现状,就要以产品难度适当、“制造边界”恰当为原则,构建职业教育“三维五环”“类型化”育人模式,以追求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地位”为目标。一是以需求分析、原理构思、技术设计、产品生产、销售服务为课程内容建构的“制造边界”;二是以技能操作、情境判断、工具选择、对象识别、规则分析为教学问题设计的技术线索;三是以生产过程体验、技术参数测定、产品功能分析、产品成本核算、运行效果评估为学生学习中问题发现的来源。从而构建起一个基于技术的“问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的学生学习自组织系统。
强调职业教育是“类型教育”,目的是突出其在认识论意义上的独特性,彰显其在教育性价值上的重要性。但是,我们不能忽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同一性,只有取长补短、为我所用,以职业教育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完美结合,才能去追求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这一永恒目标。
(作者系本报特约评论员)








 当前位置:
当前位置: 来源:互联网转载
来源:互联网转载  作者:版权所有者
作者:版权所有者  时间:2020-08-31 12:00:00 发布
时间:2020-08-31 12:00:00 发布  标签:教育资讯
标签:教育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