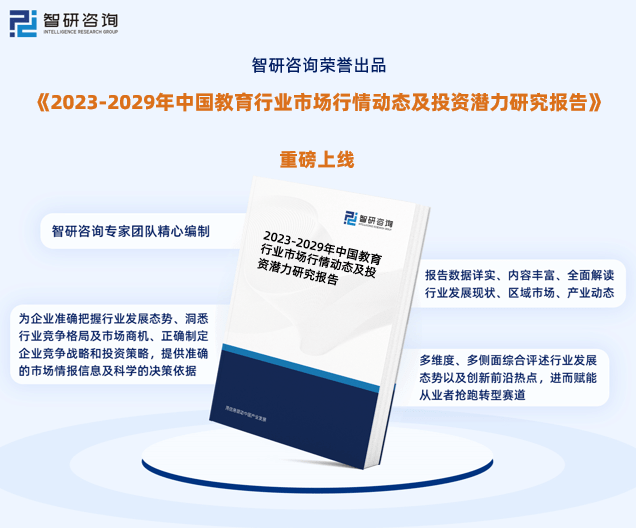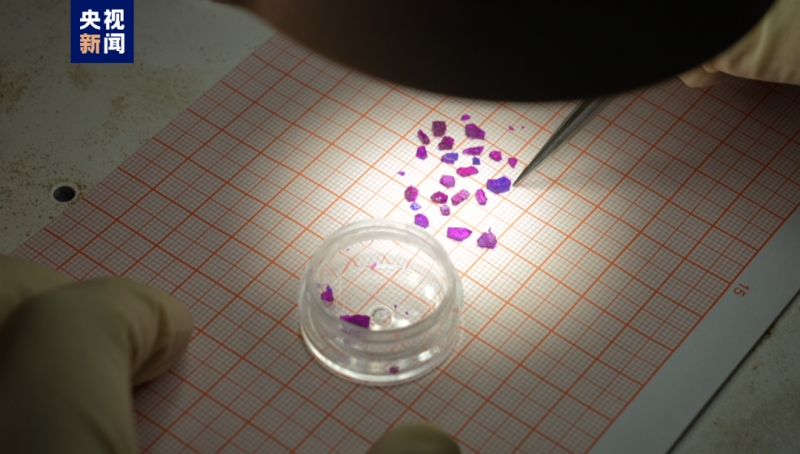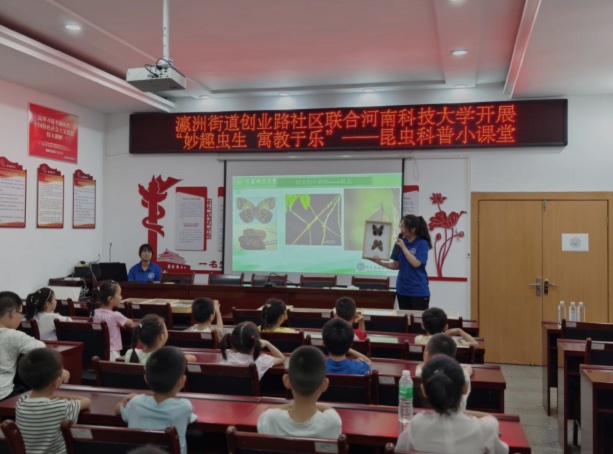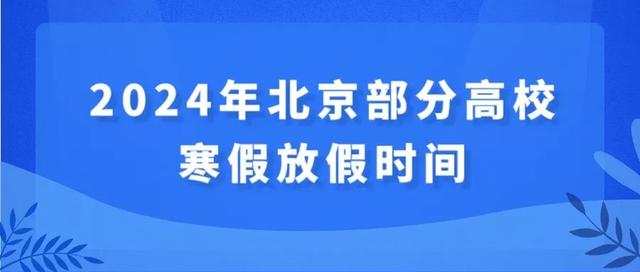近年来,为满足群众的期盼与诉求,全国各地纷纷开展“弹性放学”“校内课后托管”等多种探索。2017年,教育部出台《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为学校办好课后服务指明方向。

“课后三点半”,曾是令不少家长感到头疼的问题。
近年来,为满足群众的期盼与诉求,全国各地纷纷开展“弹性放学”“校内课后托管”等多种探索。2017年,教育部出台《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首次从国家层面为学校办好课后服务指明方向。
从教育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来看,截至2020年10月,全国已有29个省份出台了中小学课后服务政策,全国36个大中城市(4个直辖市、27个省会城市、5个计划单列市)66.2%的小学、56.4%的初中开展了课后服务,43.2%的小学生、33.7%的初中生自愿参加课后服务,覆盖面很大。但课后服务的质量如何?能否满足学生全面发展需求?如何提质升级?
学校课后服务如何回应家长诉求
每到下午放学,不少中小学门口便立起了各色各样的托管班标志牌,三五成群的学生跟随托管机构工作人员离开,或是赶向课外培训班,这似乎成为一种校园常态。
在中小学放学到家长下班的这段空白时间里,“孩子去哪儿”困扰着家长,同时催生着“课外培训热”,成为社会关注的民生问题。在此背景下,校内课后服务应运而生。
下午三点半,四川省成都市盐道街小学三年级语文教师谢祯走进教室,学生们已经自觉地拿出了作业。
“谢老师,这个问题我不太明白。”当天已经有好几名学生问过同一个问题了,于是谢祯走上讲台,清了清嗓子说:“今天的作业里有一道题目比较难,我给大家讲解一下。”
周一至周五,盐道街小学全体教师轮流辅导学生在课后服务时段完成当天作业。“如果遇到学生普遍反映的难点问题,老师统一讲解,之后再录成小视频发到班级群里,供没有参加课后服务的学生观看学习。”谢祯说。
在课后服务的两个小时里,学生做作业的效率和质量都有明显提升,家长反映孩子回家后运动时间、休息时间更充足了。“学校开设课后服务两年多来,家长从最开始持观望态度,转变为主动报名参加。现在大约有90%的学生留下接受课后服务。”谢祯说。
在同一时段,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实验小学里更为“热闹”。作为泉州市首批开展课后服务的试点学校之一,该校校长蔡晓芹告诉记者,自2018年春季学期开展课后服务以来,学校在提供看护和课业辅导基础上,还陆续增设了田径、管乐、科技等社团活动,以及地方传统文化梨园戏、南拳、木偶表演等,目前已开设39个课后服务班。
与此同时,福建省晋江市第五实验小学的学生们冲向操场。作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全国青少年校园冰雪体育传统特色学校”,体育已经融入晋江五小办学的方方面面。该校校长徐建平介绍:“学校课后服务突出对学生文体特长的培养,既有足篮排等体育项目,还有合唱、书法等艺术项目,今年还在尝试推广高跷运动。”
“目前来看,课后服务种类多样。比如提供看护服务、作业辅导、培养学生兴趣特长、辅导学习落后的学生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马健生指出,各地因地制宜地对服务内容进行了探索,但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在国家叫停“学校补课”后,重新启动的“课后服务”要如何定位?课后服务,只是填满时间这么简单吗?
在采访中,一些家长表达了自己的诉求。
北京市朝阳区的李先生就表示,开学之初,孩子所在学校教师明确表示,学校的课后服务只是让孩子放学后留在班上自习,没有学业辅导更没有体育、艺术方面的拓展活动。“孩子都坐了一天了,放学还要继续在教室干坐着,还不如让孩子回家做作业。”因此,李先生并未选择给孩子报名校内课后服务,他介绍班里只有个别选择报名的。“若学校的课后服务能提供一些文体类选择项目,我们还是很愿意让孩子参加的。”
记者采访了解到,不少家长在报名参加了一段时间学校举办的课后服务后,便选择退出,转向校外托管班,原因也在于对学校课后服务不甚满意。
有专家表示,如果课后服务只是把孩子从托管班、课外班转移到学校,进行“物理”上的改变,其实还是没有逃离“低水平”。
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教育教研室主任、硕士生导师傅添进一步指出,课后服务要起到教育作用,不仅应包括知识学习,还应注重培养和发展学生不同的兴趣、爱好、专长,或者基于学生情况和需求提供不同服务。“而从教育公平的角度来看,课后服务也应有助于缩小不同家庭背景孩子之间的教育差距。”傅添说。
如何有效调动教师参与积极性
“在没有课后服务的时候,我就习惯留下来备课,现在只是换了内容。”在谢祯看来,课后服务与本职工作并没有那么清晰的划分。加之自己的孩子已上高二,放学较晚,自己多留校一会儿“问题不大”。
“感觉最大的压力是‘逼’着自己提高工作效率。”谢祯说。
尽管许多教师像谢祯一样,出于职业责任感承担起课后服务工作,但不可否认的是,课后服务“解放”了家长,却增加了教师和学校的压力与责任。如何调动教师主动参与课后服务的积极性,保障课后服务可持续性,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对于谢祯来说,“看到自己班上的孩子做作业效率提高了,学困生追上大部队了,心里还是很欣慰的”。除了成就感,学校还让课后服务开展得好的教师做经验分享,这种精神鼓舞也让谢祯感到高兴。
类似的,在泉州鲤城实小,蔡晓芹和几位校行政班子成员每天都会对课后服务进行巡课,从教师出勤、服务态度、学生评价、家长满意度等方面综合考评,进行表彰。
“按照《泉州市推进小学开展课后服务工作实施意见(试行)》要求,学校对参与课后服务的教职工发放劳务费,人均每课时60元。”蔡晓芹补充说。
从各地关于开展课后服务工作的相关文件中,记者发现,教师参与课后服务人均每课时劳务费基本在几十元区间,有的并未明确予以教师额外补助。与之相比,校外培训市场上辅导课单课时收费远高于此。
“课后服务已经超出了教师正常工作时间,属于额外劳动。但在‘有偿补课’禁令之下,教师参与课后服务难以获得工资以外合法的劳动报酬,变相成为长期义务劳动。”马健生直言,这显然有失公平。
课后服务该由谁付费,已是课后服务提升质量的一个焦点问题。
目前,北京、上海、河北、福建等省市,课后服务由地方财政支持开展,生均拨款每年度在200元至500元之间。近日,深圳市新出台的课后服务征求意见稿更是明确提出,各学校课后延时服务专项经费预算按每生每年1000元标准作为控制数,由财政拨款。
但专家指出,通常情况下,地方财政拨款往往低于学校实际支出,一些学校的课后服务正在“负重前行”。
有教师算了一笔账:“按照‘弹性离校’安排,上级财政按每生每年300元经费拨付。如果按每周4天,每天延迟两节课计算,每学期至少延迟80节课,一学年就要延迟160节课,计算结果是每节课补助不足2元。再加上学校水电费、消耗品购置等开销,服务经费使用紧张。”也有校长表示,经费不足使得学校难以邀请专家、校外机构支持课后服务,提质升级有心无力。
一些地方探索了费用分摊机制。比如广州、海口、成都等地都明确规定可采用收取服务性收费或代收费的方式筹措经费。
对此,马健生解读,课后服务在义务教育的公共属性范畴之外,“谁享受谁支付”是一种社会理性。“如果政府包揽,一方面增加财政负担,另一方面也让家长感到‘理所当然’,影响家校关系。而通过让家长支付一定费用,反而可以帮助厘清课后服务中的权责关系。”
但马健生也看到,如果“课后服务”“课后补课”等概念没有重新界定,那么课后服务收费与提质将始终行走在危险边缘。
傅添同样表示,如何保障课后服务的质量与可持续性,必先回答其究竟“是不是学校必须承担的责任”“是不是学校必须提供的教育服务”之问。“如果是,那么应当将课后服务纳入学校和教师的日常工作体系,从制度、经费、考核标准等方面来保障和提升教师参与度和完成质量。但如果不是,那学校和教师就没有法定义务和责任来提供高质量的课后服务,学校也就只能依靠软性的方式来鼓励教师参与课后服务,比如思想动员、经济补贴等。”傅添说。
马健生建议:“待政策予以明确后,工商部门与教育部门可以参考市场价格,共同对看护、学业辅导、兴趣特长培养等不同服务类型,确定区域性服务费用。”
如何发挥家校社协同治理作用
社会对高质量课后服务的诉求,在实践中转化为对师资的更高要求。一些学校将目光投向校外。
放学后,在泉州鲤城实小通淮科技馆的悬浮星系区、VR体验区、3D打印创新区等多个功能区里,学生们正在动手做实验。
“在鲤城区科学技术协会支持下,我们的课后服务开设了科技社团,本学期还开设了机器人社团、编程社团。”蔡晓芹介绍,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泉州市提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也派出辅导员,一同为学生提供课后服务。“这不仅可以丰富课后服务内容,还可以弘扬传统文化,坚定学生文化自信。”蔡晓芹说。
此外,哈尔滨市教育局与哈尔滨学院、基层学校启动了政府、高校、中小学三位一体的课后服务项目,大学生为课后服务注入新的活力;上海市整合街镇社区学校、其他社区服务公益性组织等各类社会资源,为学生提供放学后的看护服务;石家庄市组织高素质社区志愿者进校参与托管;青岛市发动学生家长、退休老教师等群体参与课后服务……
但这并不代表家校社多方协同参与课后服务已水到渠成。
“我们正在考虑,邀请部分学生家长、社区志愿者来学校一同参与课后服务。但是要这样做,再小心谨慎也不为过。”徐建平说出了校长们共同的顾虑。第一,如何保障安全?第二,家长、社区志愿者等人员固然热心,但如何确保其言谈举止符合教育教学规范?第三,校外人员并未获得教育资质认定,如何保障服务质量?
一边是紧迫的需求,一边是现实的困难,建立有效的协同治理机制要如何作为?
“我们正在从零起步。”傅添表示,当前家校社合作主要围绕传统校内活动,对于三点半后的课后服务如何合作,还是一个比较新的问题。
傅添认为,首先要为课后服务确定目标。“这个目标是由学校制定,还是由县市制定,还是全国统一?我认为不该一刀切。政府可以先制定指导性原则,再由各校因地制宜、结合家长需求来确定。只有确定了目标,才能确定谁来服务。”
对于家长“过多过热的需求”,傅添表示,若只关注需求而忽视学校客观能力的有限性,难免衍生矛盾。“家长在制定课后服务目标上享有参与权。学校要充分听取、参考家长建议,但最终应该由专业的教育工作者决策。这是学校自主权的体现。”傅添说。
参考国际上“课后三点半”问题治理经验,马健生指出,英美等国家借助多方资源协同开展课后活动项目。例如,美国很多地区成立学校家委会,申请独立免税账户,由家委会决定放学后活动的经费收支、拨付方式等,以便保障各类服务人员的合法权益。
因此,马健生建议,发挥家长参与学校治理的积极性,建立更畅通的家校共治参与机制。“这既有利于现代学校的建设与发展,也符合家长参与学校治理的迫切期望,相得益彰。”
谈及整合社会资源参与课后服务伴生出的安全与监管问题,有学者分析,相关法律规定,在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之外,学生由家长作为监护人负责管理。但当涉及学校课后服务,则变得复杂起来,因为这是政府管理权、学校办学自主权、家长监护权、教师休息权的交集领域,目前仍存在许多法律责任不清甚至空白的地带。谁来管?如何管?
“只有先从法律政策上确定课后服务的性质和目标,然后才能解决各主体、职权责、监管、考核与评价等一系列问题。”傅添说。
马健生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虽然课后服务看似是一个小问题,但关系各个家庭,牵涉社会福祉。对课后服务法律法规进行系统梳理与调整,理顺课后服务与‘义务教育’‘学校补课’‘学生减负’的关系,明确其内涵,势在必行。”








 当前位置:
当前位置: 来源:教育信息网(转载)
来源:教育信息网(转载)  作者:版权所有者
作者:版权所有者  时间:2021-01-06 12:00:00 发布
时间:2021-01-06 12:00:00 发布  标签:教育资讯
标签:教育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