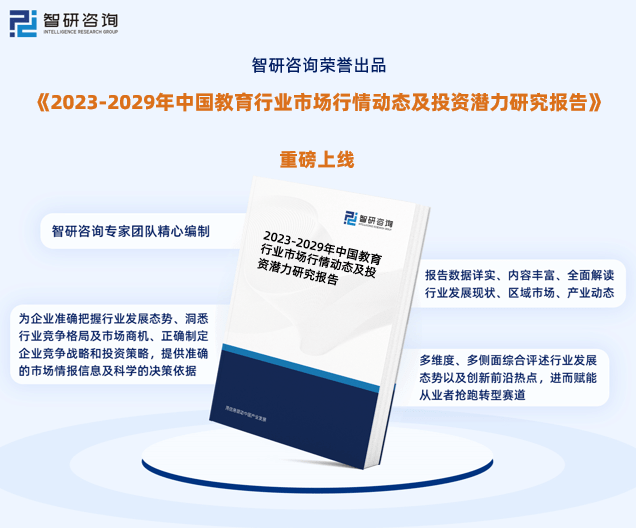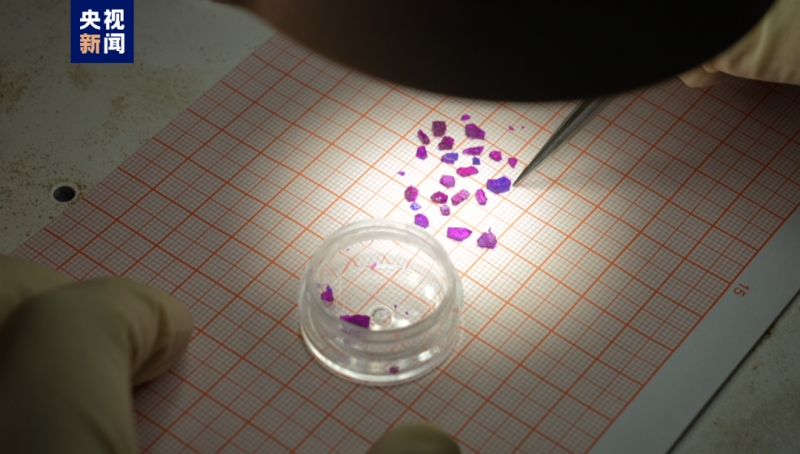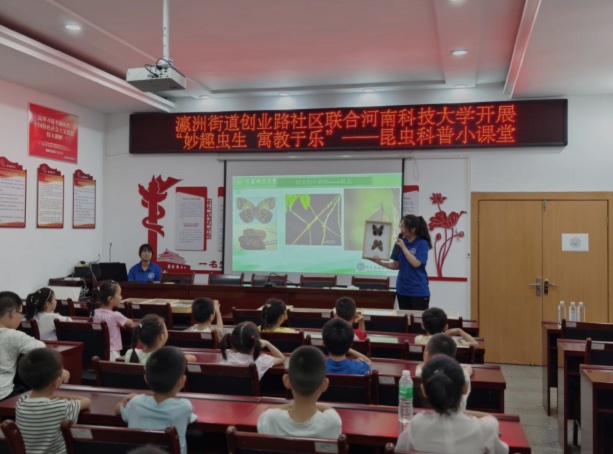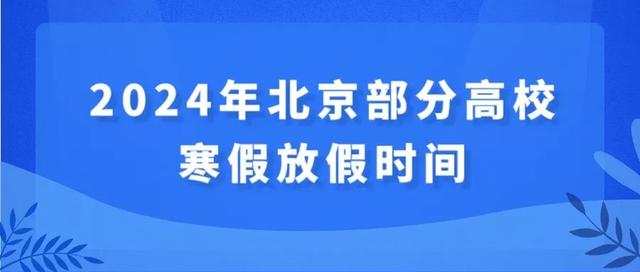近代以来的哲学,都是在科学理性的大背景下建构起来的。而蒙培元先生的学说,学界一般将之归结为“情感儒学”,或者再延伸一点称之为“情感哲学”,以“情感”作为主题词来归纳他的思想或表达其学说的主旨,特色非常鲜明。科学理性的思考方式和绾结的系统与我们今天所讲的“情感”内容,实际上是有所剥离的,因为一般讲的哲学是理论思辨的、是逻辑推论的,而不是“自然”的流露,更不是所谓“本真”的状态。比如讲“情感”问题或者主张唯情主义,可能从美学、文学的方向上理解的比较多一些,而很少从哲学本体或者认识论的角度来切入。
20世纪中国哲学体系的建构,一般也是基于“理性”的原则,而理性和情感往往就构成一种对反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情感”何以能成为“本体”或者成为哲学理论的基础?由此,蒙先生的一些思考和说法,包括给“情感”以很高的定位,讲“人是情感的存在”。这样的命题,在今天重视本体、以理性为基础的哲学系统中,的确是比较特殊的、也可能是引人注目的。所以,“情感”作为哲学本体或在形而上的意义上何以可能?它的理论基础何以建立?而这方面的思考和孟子所开创的心性一系有很大的关联性。
实际上,情感与理性的关系,在整个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长久被思考的问题,也是不断在讨论的一个话题。譬如在孟子的思想当中,他要处理自然感知的问题,也要解释“亲亲”感觉的特殊性。既有口之于味同嗜、耳之于声同听、目之于色同美的“同然”之感,又有面对“亲亲”关系时的超自然感觉,它是本之于理、义的“心”,而不是感官。前者可以成为理性建构的基础和逻辑认知的前提,而后者只能从心性与情感的语境当中来理解。血气心知是属于功能性的,构成了同类之间相互交流与沟通的基础,所以它是一种同类相感;而“亲亲”之间的相怜相惜、手足之情是超感觉主义的,是一种唇齿相依的共通感,属于心有灵犀。从认知活动的普遍性来讲,同类相感可以作为建构本体的基础,那“亲亲”之感如何超越个体而成为共有的存在,或获得存在本体上的意义?孟子实际上就面对了这样的困境,在《孟子》文本中就包含了这样的两层分疏。如果我们拿蒙先生讲的“情可以上下其说”来看这个问题,可能会得到一些启发,对“情感”何以能够成为本体,也会多些新的理解。
在《孟子·万章上》有一段师徒间的问答。万章问:“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何为其号泣也?”孟子以“怨慕”答之。万章引了曾子的话“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说:那舜还“怨”什么呢?孟子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引了曾子的学生公明高与其弟子长息之间的一段对话来解释之。在这个理解和解释的语境中,“情感”就不是简单的自发状态,或者只是喜怒哀乐的自然发抒,而是关涉到了生命的存在本质。向天而泣之寓意,赋有深刻的本体论意义。通过诠释“舜号泣于旻天”的事件,孟子实际上是要给“亲亲”的原则找到一个超越的理据,为人的存在性做出一个目的论的说明,或者说为人伦关系的天然性与内在性确立一种形而上的意义。人的生命所自出,人的存在价值的根源性何在?确立人之为人的主体性又是什么?这些先验存在的追问,只能从“亲亲”原则来加以理会和说明。所以,孟子在讲这种“亲亲”之感的时候,尽管这也是一种“情感”,具有可以感知的特征和经验的体证性,但它已经不局限于生命个体的经验世界,更不是人之情欲的自然状态,而是把这种情感提升到了与天地同流、与天地共在的境地。孟子讲这件事情,是从人的来由、人之存在的价值根源,来思考和解答之的,因而是一个形而上的追问。所以他说:“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其竭尽全力所打造的舜的道德典范意义,其根本要义便在于“大孝”。故谓“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是知二者之根本,礼是调节而顺处之,仁义礼智“四心”皆是以“亲亲”作为根基和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亲亲”之感就不是一般的感知,也不是从普通的情感状况来申述人的自然状态,而是包含了很强的超越性和神圣性,是对人的存在的根源性之思,这就为基于人伦理解的道德情感奠定了一个形而上的基础。
和道德情感的形而上建构不同,同类相感是源于人的自然性能,是“血气心知”的必然导出,它服从于一个类推的原理。“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人人都具有这种感知能力,在相似的经验活动和认知过程中,人人都可以得到相同的体会和认识,所以是心有同然、物有同理焉。这种“感知”的类推逻辑,可以达成某种共识,建立起知识的普遍有效性,从而形成我们对外部世界所共有的看法。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知识形态建构的过程,是通过“知识心”的理解来说明人的客观境遇,展示人所具有的类本质。同类相感为个体生命之间的连接提供了可能,通过这种认知方式,不同的生命个体得以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社会共同体。
《孟子》中的这两层分疏,提示我们对“情感”可以做不同的理解,除了一般感知功能的同类相感之外,在“情感”的深处,实际上也包含了某种对存有意义的追问和形而上的超越之思,这就是对“亲亲”原则的特殊理解。通过对此“亲亲”之感的诠释,我们可以把“情感”放在一个本体的高度来解释,可以由存在论的根本义理来说明。这也许便是蒙先生所讲的“人是情感的存在”命题的要义所在。这一形而上色彩颇浓的命题,表明了“情感”作为哲学本体的可能性,也揭示了“情感”所含具的更为深刻的本质意义。关于这些思考,我们可以从《孟子》文本已经包含的两层分疏当中,得到一些印证和体会。
情感儒学显然不是从同类相感的认知意义上来立论的,而是强调了人的道德主体性和超越精神,是对人的道德情感的一种展开和说明。道德理性构成了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的一个根本内容,也可以说是整个儒学的核心部分,所以将儒家的学说归结为“情感儒学”,可能并不为过。在一定程度上,蒙先生讲的“情感的转向”是有明确所指的,是一个标志性的提法,即在20世纪理性主义占绝对上风的大背景下,怎么来容纳非理性的东西,重树“情感”的价值主体性。这样一种哲学思考,和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从历史上的一些资源、从儒家思想的特点入手,来重构当代哲学的问题、对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做出新的阐释,无疑是有价值的。这也确实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因为人不只是理性的动物,也是情感的动物,尽管我们今天讲哲学,基本是从理性的原则和意义来着手的,但人的存在的多层性、复杂性,生命活动的一些特殊之处,包括它的本始意义——这些可能都是我们今天讲哲学需要去思考和面对的问题。所以如何从道德情感出发,来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的体系,蒙先生是开了先河的,他的思考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探索,他所开辟的方向在未来中国哲学发展的途程中,一定会有更加辉煌的接续。
(作者:景海峰,系深圳大学国学院教授)








 当前位置:
当前位置: 来源:教育信息网(转载)
来源:教育信息网(转载)  作者:版权所有者
作者:版权所有者  时间:2022-07-11 09:59:44 发布
时间:2022-07-11 09:59:44 发布  标签:教育资讯
标签:教育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