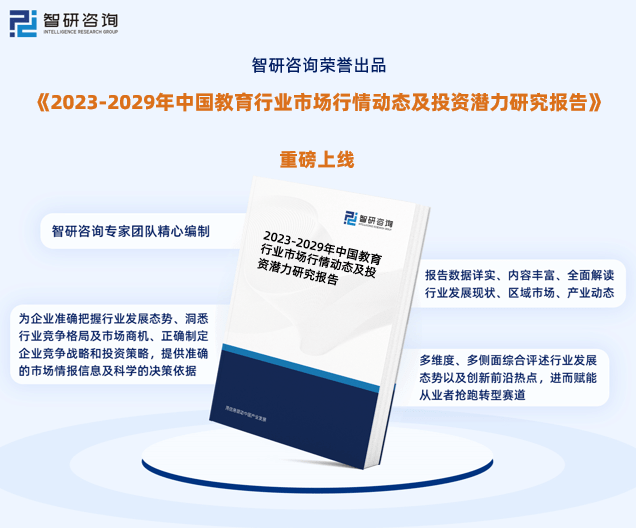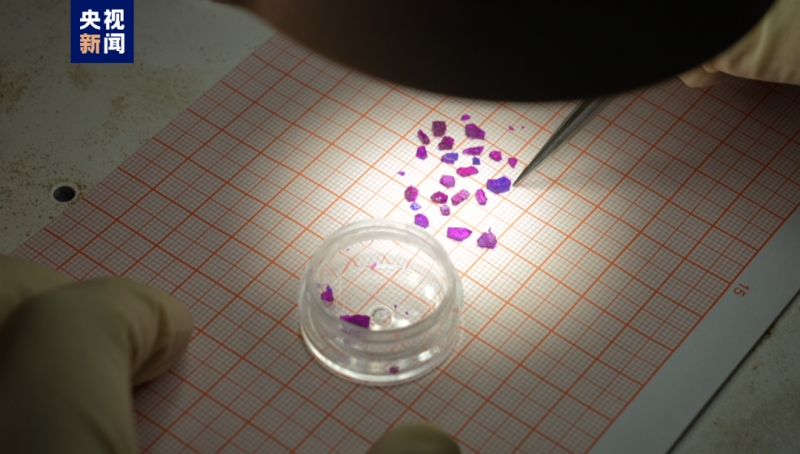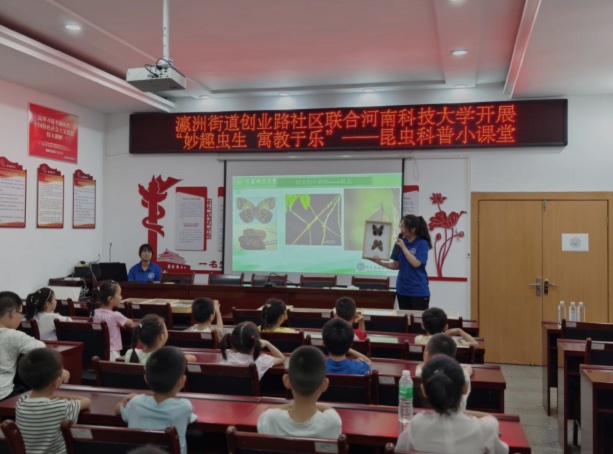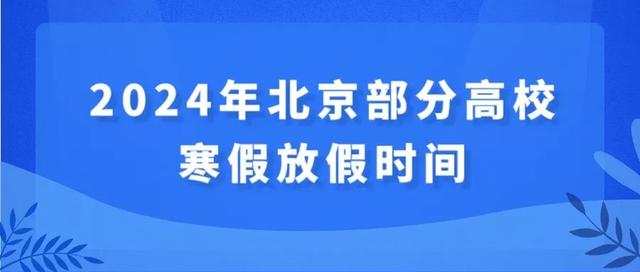现在,消费者数字化正在倒逼生产者数字化,学校教育正在把媒介和数字素养列入学生的能力框架。数字素养是对媒介和信息素养的新发展。
大众的读写能力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文字读写能力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主要封闭在宗教、商业、政府、科学等工具的和专家的用途之中。英国学者霍加特认为,随着大众期刊的出现,文字读写能力出现了服务大众娱乐需求的用途。随着杂志、广告、电视、数字化媒介等多模态交流方式的凸显,随着经济全球化对全球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的推进,提高媒介读写能力进入议程。进入Web2.0时代,“只读”变成“读写”,“写作”与“阅读”一样普遍,媒介读写能力不足以描述私人化数字读写的复杂性,大众数字读写能力的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引发关注。
大众数字读写的热情与“DIY文化”(DIY是“Do It Yourself”的英文缩写,意思是“自己动手”)合流,抖、秀、播、拍、聊、赞、转等数字读写文化现象,在社交网络蔚为壮观,庞大生产消费者(prosumer)群体井喷式发展,青少年则是主要参与主体。数字读写文化的积极作用有三:一是为青少年提供了表达和社交的机会;二是丰富了青少年的文化生活;三是发展了青少年的数字文化素养。乐观主义者甚至认为,数字读写文化体现了新价值观、新知识和新型社会关系,以数字读写能力为核心的创意产业将掀起一个新的“漫长的世纪”。经济学家拜因霍克认为,基于“无标度”的复杂体系,消费者联合起来,“大家动手”(DIWO)将是未来财富的起源。
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科学认识当前大众数字读写文化,有几个问题需要反思:一是对照“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这一目标,当前娱乐化的数字读写文化是否达到了要求。二是当前众声喧哗、呕哑嘲哳的大众数字读写文化状态,到底有多少经济潜力和创造力硬核。三是私人化的端对端数字读写文化,是否会导致网络社群的审美趣味不断分化、社会参与热情度降低,形成美国学者帕特南所谓的“网络巴尔干化”和“独自打保龄球”化。四是当前数量庞大、声势浩大的数字读写文化,是不是年轻人真正自觉自主的文化,是不是他们创造的最好的文化、最需要的文化。青少年是网络文化的主体,互联网是他们自我表达、自主创造的新天地,但任何文化都需要在引领和培育中生长,年轻人热衷的数字读写文化也需要与先进文化、主流文化、精英文化根叶相簇、呼吸相通。年轻人如何读写、读写什么、读写的审美标准何为?这些问题需要引导。
我们要把数字文化素养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
现在,消费者数字化正在倒逼生产者数字化,学校教育正在把媒介和数字素养列入学生的能力框架。数字素养是对媒介和信息素养的新发展。数字素养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作为生存技术的素养,包括数字信息理解、数字环境交流、数字工具使用、数字安全意识等;另一方面是作为文化实践的素养,包括基于数字工具的自我表达能力、高雅的数字文化品位、健康的数字社群关系等。数字文化素养培养的目的是,把青少年培育成健康的文化实践主体。
数字读写文化素养培养可以与国家的相关教育行动相结合。2018年,教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中小学影视教育的指导意见》指出,把影视教育作为中小学德育、美育等工作的重要内容,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与学科教学内容有机融合。数字读写文化的引导可以和影视教育相结合进行。
社交媒体的数字读写文化要建立导向机制。
一是实施专门化的数字讲述活动。数字讲述是指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以工作坊为基础的文化实践,旨在教会人们使用数字媒体制作短视频以讲述自己的生活。这项运动在国外已经成为一种公共部门倡导的事业,全球很多国家建立了数字故事中心的门户网站,有社群交流分享的“数字故事圈”。我国的数字讲述还只局限于教育教学领域,我们应调动各方面力量把数字讲述介入网络文化领域,用以引导大众数字读写文化。
二是网络平台和媒体精英担起社会责任。网络平台和媒体精英在获益于互联网的同时,还要积极回馈互联网,发挥数字读写文化职业生产内容(OGC)和专业生产内容(PGC)的引领作用。
三是形成道义化契约。引导青少年树立数字读写的版权意识,借鉴美国学者詹金斯在《融合文化》中提出的“网络道义经济”思想,通过技术手段形成一种服务于知识共享的契约文化、道德文化,优化数字读写文化的生态性发展。
四是建立制度化底线。数字读写文化也要建管结合,发挥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协会的制约作用。如2019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的《网络短视频平台管理规范》等,都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化保障。
全力推进数字读写文化的学术议程。
相对于数字乐观主义,数字文化研究学者特纳、洛文克等从商业操纵角度,特拉诺娃、安居杰维克等从数字劳动角度对数字民主迷思进行批判。特纳认为,“数字讲述运动”是一种积极文化实践,它说明学术工作如何开发人们真正需要的能力。哈特利和麦克威廉《故事圈:全世界的数字讲述》一书描述了世界范围内的数字讲述实践,但新媒体环境下的相关研究还不够深入。
西方学者把全民读写能力作为一种“具有推动力的社会技术”,本质上是强调一种文化政治实践,有其意识形态特点。中国的数字文化实践和研究,需要立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于中国梦实现的伟大目标,立足于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立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立足于中国互联网的健康发展,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
数字读写文化与互联网的“下半场”,具有一致的研究议程。互联网的“下半场”一方面要平台化、移动化、智能化深入发展,一方面还要反思和解决“上半场”暴露出的问题。一是改变网络文化的娱乐化、商业化功能脱嵌状态,守护文化的真正功能、复合功能。二是打破“泛用户中心主义”和数字民主的迷思,使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服务于具有文化自觉、文化自主、文化自信、文化创造素质的人的发展,而不是服务于商品化的、消费化的、异化的人的规训。三是要廓清创意文化的边界,使“人人参与”和“大众意义创造”的非物质劳动,形成有时代价值的“硬核”。
(作者系吉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本文系2018年度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网络文化专项重点委托项目]“吉林省和吉林省涉东北亚网络舆情与管控研究”[2018W5]成果)








 当前位置:
当前位置: 来源:教育信息网(转载)
来源:教育信息网(转载)  作者:版权所有者
作者:版权所有者  时间:2019-03-21 12:00:00 发布
时间:2019-03-21 12:00:00 发布  标签:教育资讯
标签:教育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