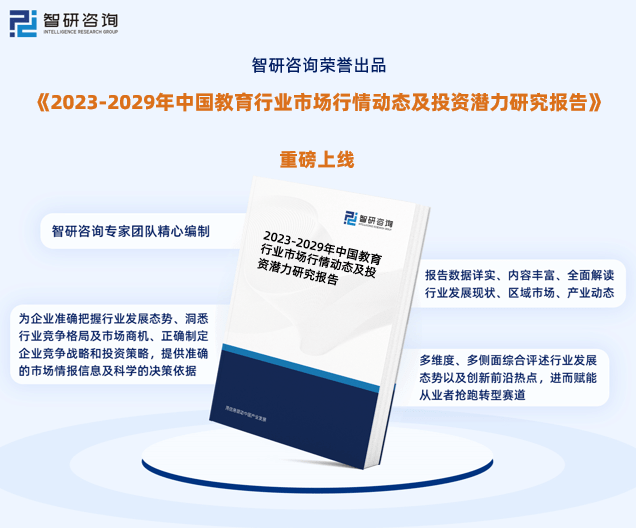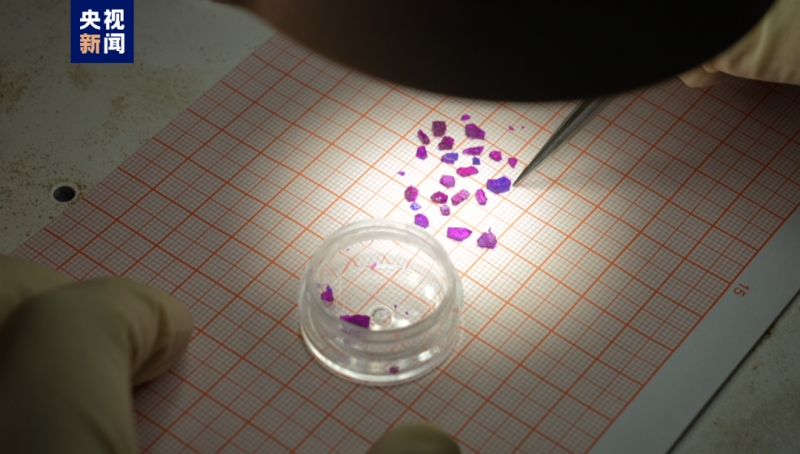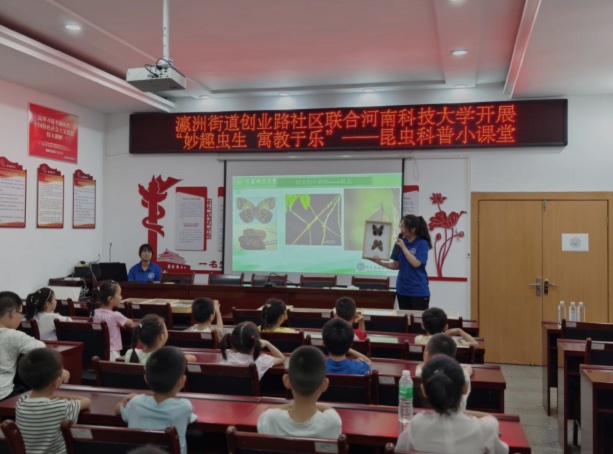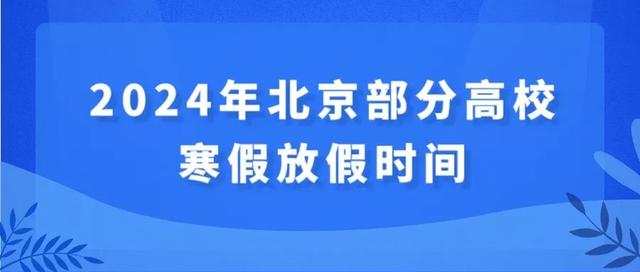科技改变教育,教育离不开科技,但教育不应为科技所困。在新技术助推教育发展的同时,我们忽然意识到:慕课的黄昏似乎会比预料来得早。
作为新形态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慕课乘上了教改时代的过山车。2013年5月,清华、北大率先加入美国慕课平台edX,次年“学堂在线”“好大学在线”等中文慕课平台相继问世,短短一年,八个平台迅速成立,火热程度可见一斑。CSSCI文献统计显示,2014年以慕课为主题的文献较前一年增长七倍多。edX总裁阿加瓦尔提出“慕课是人类教育史上的首次革命,将重塑高等教育的模式”。但与此愿景形成强烈反差的是2013年“反慕课”的声音迅即出现在西方知名高校中,有高校声称退出慕课平台。2013年5月,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的58位教授联名给院长写信,要求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指导“在线课程”产生的问题,包括从教师监管到对整个高等教育体制的影响。2013年11月果壳网完成的“MOOC中文用户大摸底”的调查数据,只有约6%的用户最终完成了课程学习,远低于校园内有组织的课堂教学。高退学率/辍学率、潜水者、“僵尸注册用户”现象直指慕课所标榜的“高效率”核心特征。如果进一步质疑的话:慕课真的是课程吗?瞬间起落的危机恰好印证了慕课与教育目标间的裂痕。
对“慕课”现象的反思首先源自对课程存在意义的追问。泰勒在《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中明确表达,教育活动是围绕着教育目标的设定而产生的,教育目标的设定是决策者有意识的对各种价值选择的过程。一方面课程作为最重要的教学计划是达成教育目标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通过对课程的科学研究,能为决策者明智地选择目标提供适当的基础。由此看来,课程设置与开发的起点是教育目标,只有围绕目标,课程的设置才有意义。毫无疑问,教育因人而生,教育以人的发展为鹄的。吴万伟认为慕课起源于私有公司,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旨在将传统学习模式应用到信息技术上来开辟新市场,通过远距离传输课程给数以万计的学生,试图通过数字技术取代或等同于大学课程,这种极端的想法发生在传统大学理念日渐式微的情形之下,短时期内着实具有煽动性。但是,正如圣母大学教授帕特里克·迪恩所言,慕课不过是几十年来处于现代大学核心的一些趋势的自然延伸而已。
为了使课程最大程度为教育目标服务,课程组织实施显然是关键因素,它极大地影响着教学效率。课程组织的连续性、顺序性和整合性至关重要,课程设置至少包括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面对不同的学习者,同一课程的难易顺序、不同课程的组合方式以及课堂的有效组织是决定学习效率的关键。慕课声称“以学习者为中心”,实则无法顾及学习者主体间的差异,以互联网为依托,慕课的授课对象可以无限延伸,这种在线与开放的特性使得学习者的主体地位无从确立。再者,标准化教学把创造性地讲授框定为机械的信息程序,正如芝加哥大学教授马萨·诺斯鲍姆所说“令人悲哀的教学转向,即从推动质疑和个人责任转变成为了取得好成绩而灌输”。能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连接网络的信息技术更好地满足了受教育者对教育实用性的期待,教育工具化的结果必然使得受教育者变得功利与现实。在慕课的世界里,学习者是孤立与随意的。杜威强调:“学校必须呈现现在的生活,不通过各种生活形式或者不通过那些本身就值得生活的生活形式来实现的教育,对于真正的现实总是贫乏的代替物,结果形成呆板而死气沉沉。”慕课缺少了课程组织中人的因素,而这正是传统教育的魅力所在。
课程评价有两个重要指标,一是知道学习者的行为起点,衡量学习者的行为终点,从而作出评判。二是评价的方式不仅仅指考试分数,还要包含行为观察、实际操作、情境处理等。现行的慕课,课程考核无法测量学习者的行为起点,考核方式单一且无法验证。测试方法包括机改、测试与评议。无非就是使用机器来批改多项选择题,加上通常意义上的出题考试,再辅之以同学之间互相批改那些承接于网络的论文任务。实践下来,这些测试的成效都不大,其中最大的难点是无法有效地防止学生作弊,网上测评缺少有效的防范措施。
科技改变教育,教育离不开科技,但教育不应为科技所困。在新技术助推教育发展的同时,我们忽然意识到:慕课的黄昏似乎会比预料来得早。
(董云川系云南大学教授,云南省政府督学,云南省高教学会常务副会长,省高教评估事务所所长。专注于大学精神及教育改革发展问题研究)








 当前位置:
当前位置: 来源:教育信息网(转载)
来源:教育信息网(转载)  作者:版权所有者
作者:版权所有者  时间:2016-05-30 12:00:00 发布
时间:2016-05-30 12:00:00 发布  标签:教育资讯
标签:教育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