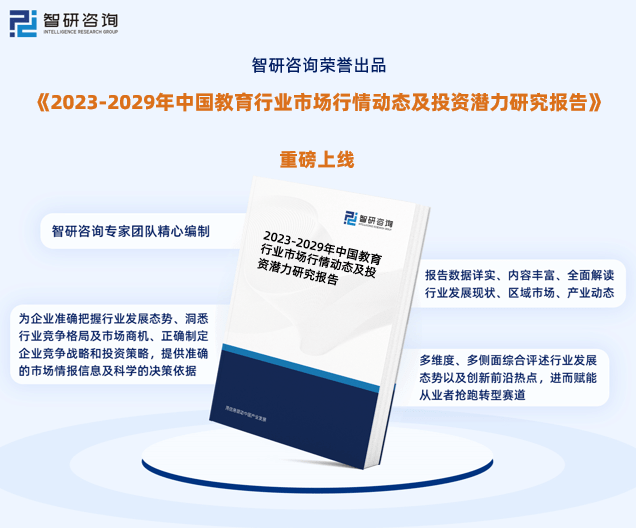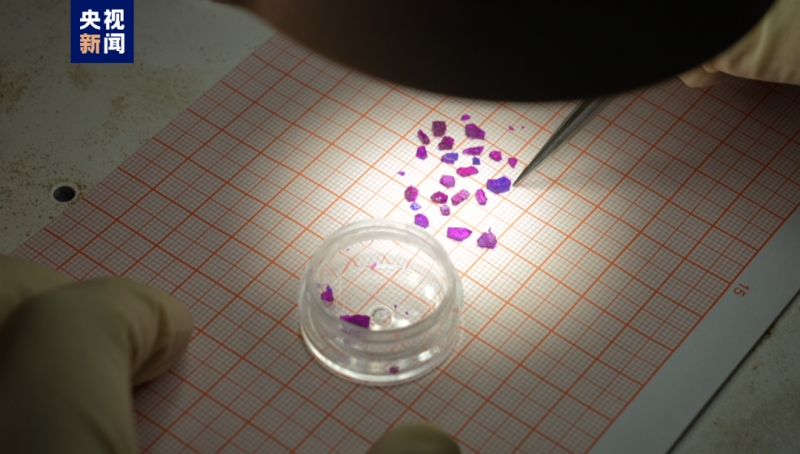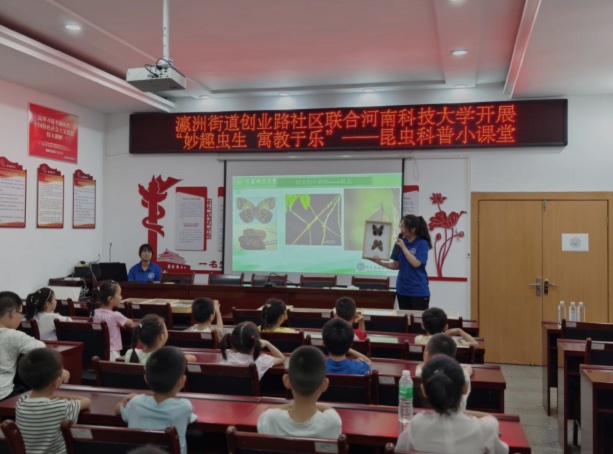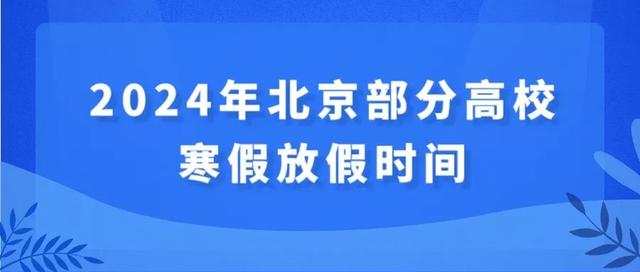米尔恰·伊利亚德是与齐奥兰(EmilCioran,又译萧沆)同时代的罗马尼亚裔文化人,晚于大名鼎鼎的罗马尼亚裔雕塑家布朗库西,但早于罗马尼亚裔小说家诺曼·马内阿(NormanManea)。伊利亚德与齐奥兰经历多少有些相似,并且都习得了法国文人传统的博学、多面的特征。他在二战后的法国学术界站住脚,得益于宗教学家乔治·杜梅齐尔的荐引。但伊利亚德后来去了美国芝加哥大学,他以法语写成的学术作品也被大量译成...
米尔恰·伊利亚德是与齐奥兰 (Emil Cioran,又译萧沆) 同时代的罗马尼亚裔文化人,晚于大名鼎鼎的罗马尼亚裔雕塑家布朗库西,但早于罗马尼亚裔小说家诺曼·马内阿 (Norman Manea) 。伊利亚德与齐奥兰经历多少有些相似,并且都习得了法国文人传统的博学、多面的特征。他在二战后的法国学术界站住脚,得益于宗教学家乔治·杜梅齐尔的荐引。但伊利亚德后来去了美国芝加哥大学,他以法语写成的学术作品也被大量译成英文,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宗教史学科典范和集大成之作。
米尔恰·伊利亚德(1907—1986),罗马尼亚宗教史学家、哲学家、科幻小说作家,被认为是现代宗教史学的奠基人之一。
其实,伊利亚德在罗马尼亚时期就以小说闻名。
近年来,随着弗朗西斯·科波拉导演的电影《没有青春的青春》上映,伊利亚德的同名原著小说——法语版名为《一个世纪的时间》——也一度成为热点。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还有《孟加拉之夜》和《克里斯蒂娜》。
伊利亚德的小说充满宗教的奇幻色彩。他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仿佛一体之两面。在这个意义上,他后来的学术研究仿佛是他小说写作的延续,因为二者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探索精神救赎的奥秘,比如,运用伊利亚德的术语,如何在现代社会重新认识人类生命的“超历史性”?或者,说得更文学一点,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也能获得神秘甚至神圣的启示?要知道,结果吉凶难测,充满玄机。在这方面,诗人和宗教学家兴趣类似。在《形象与象征》的序文中,乔治·杜梅齐尔就说,伊利亚德“首先而且始终是一位作家、一位诗人”。
撰文丨王东东
对伊甸园的乡愁
伊利亚德年轻时在印度学习梵文和哲学,由于与导师女儿暗生情愫而被逐出师门——小说《孟加拉之夜》即以此为灵感来源——后又在喜马拉雅山下静修,练习瑜伽,这些精神体验无疑影响了他对宗教的理解。《没有青春的青春》中的男主角多米尼克一心想要找到宗教的起源和语言的起源,这一回溯的过程本身体现了比较宗教学和比较语言学的发展线索,他爱上了与自己的初恋情人长相一样且具有通灵能力的维罗尼卡,但后者由于通灵而急遽衰老,于是多米尼克不得不放弃对起源问题的执迷。他虽然没有找到语言的起源,但与维罗尼卡的相遇却宛如重返了伊甸园。多米尼克身上有伊利亚德的影子,且投射了伊利亚德的爱情幻想和宗教想象。《孟加拉之夜》在学术上的对应物应为《不死与自由——瑜伽实践的西方阐释》。与尼采受佛教影响的“永恒轮回”观念不同,伊利亚德的“永恒回归”观念指向了人类创世神话及其主题的不断重复。这其中就集中体现了对天堂乐园的乡愁(nostalgia for paradise)。
《没有青春的青春》海报。
这是一种宗教乡愁(religious nostalgia),也是一种本体论式的乡愁(ontological nostalgia)。伊利亚德的《神圣与世俗》就沉浸在这样一种伊甸园乡愁的氛围中。它是一部宗教类型学和宗教史学研究,与之相比,《永恒回归的神话》同时还是一部历史哲学著作。无疑,基督教神话成为他观察其他宗教的起点,虽然他极力摆脱欧洲中心主义。他注意到神圣显现的不同方式,其中既有偶像崇拜和拜物教的形式,也有“印度关于化身的神学或道成肉身的至高奥秘”,换言之,既可以是一棵树、一座山等显圣物,也可以是耶稣·基督这样的人格神。由此,神显(hieophany,亦即神圣显现)概念就可以将形形色色的宗教经验及其形式一网打尽,从而实现伊利亚德宗教史学的普遍主义主张。
伊利亚德在《神圣的存在:比较宗教的范型》中详细讨论了神显的概念及其各种形态。神显形态或显圣物有:天、太阳、月亮、水、石头、大地、女人、植物、圣地……以极端的唯名论方式,它们构成了这本书的章节内容。而每一章又分为若干小节,仅以石头而论,又进一步分为:葬礼巨石、具有丰产作用的石头、“蹭石”、“雷石”、陨石和石柱、圣石等,这种分类方式几乎要遭到博尔赫斯的嘲笑了,但却充分体现了伊利亚德接近东方宗教的雄心。
伊利亚德的三卷本《宗教思想史》差不多是同一种写法,但更多了历史演进的线索,第四卷本打算论及“基督教的扩张、中世纪的中国和日本的宗教”,但由于他年事已高,又因为相关文献毁于祝融之手,不得不作罢。伊利亚德显然注意到了神显的差异性或曰丰富性,就像一个狡狯的普罗透斯,神显概念的纯一迷失于显圣物的杂多之中。神圣显现/神显的概念终于现身为柏拉图式的理念概念,对应于“神的流溢”,甚至类似于诗人根据灵感作诗。论其一生功业,如果借用以赛亚·柏林的术语,伊利亚德可谓是一个伪装成狐狸的刺猬。
诗学品格
亚里士多德有政治人的假设,亚当·斯密有经济人假设,伊利亚德则有宗教人的假设。伊利亚德反对宗教化约主义将宗教还原为社会或心理因素,认定宗教现象只能以宗教的方式才能被理解,但实际上他经常陷入同义反复。他发明了“神显辩证法”来应付反对意见,试图一劳永逸地宣称:“神圣在某种世俗事物中显现自己。”(《神圣的存在:比较宗教的范型》)。神圣的概念本身的确具有普世性,超出了基督教的范围。也因而,他的皇皇巨著具有时空上的巨大野心,结果似乎显得铺陈有余而论证不足,但这并不减损他的魅力。它们本身就是描述性知识而非规范性知识,是对地球上一切“神显”现象的博物学收集和类型学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试图达到的深度的哲学理解。他似乎相信人类宗教心智的那颗钻石相互映射的平面可以多至无限。他的书多以断片形式写成,构成了宗教的百科全书。那些篇幅不大的作品更形完美,《形象与象征》就是如此。
《形象与象征》,[罗马尼亚]米尔恰·伊利亚德 著,沈珂 译,译林出版社,2022年4月。
伊利亚德排斥宗教现象学而标举宗教史学,但实际上他得益于宗教现象学颇多。在整体上,他似乎离现象学较远而离解释学更近。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解释学,在他的著作中,难道不是充满了那种本质直观的成分,尤其是他对宗教形象和象征的分析?话说回来,解释学似乎成了人文学科的主要方法,并且也反过来捍卫着人文学科的尊严。难怪伊利亚德辩称,宗教史研究其实是一种新人文主义。它意味着后宗教时代人类对神圣之物的渴求,以及对人类心理和精神的整合。在这个意义上,伊利亚德延续了卡尔·荣格的思路。伊利亚德的宗教史著作动人心弦,与其心理和精神深度不无关系。他有意重建人类宗教的巴别塔。
如果说,伊利亚德的神显尚有一种本质主义的对于概念的执著,他无比开阔的历史视野则弥补了这一遗憾。当然,他也将对令人眼花缭乱的材料的分析上升到“原理”的层面。《形象与象征》就是对一系列神显“原理”层面的刻画,是高度优美的形式主义的炫技式解读。正如杜梅齐尔所说:“事实上象征主义这一主题在宗教思想界,乃至在整个思想界都蔚然成风。”伊利亚德对宗教的象征主义分析显然超越了荣格。它同时具有一种诗学品格,就如曼陀罗一样文质兼美。正如伊利亚德所期望,它还将对文学和心理学产生影响。对于伊利亚德来说,这也是一部对文学和心理学、符号学和图像学作出最大让步的宗教史著作。








 当前位置:
当前位置: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作者:版权所有者
作者:版权所有者  时间:2022-08-04 02:04:25 发布
时间:2022-08-04 02:04:25 发布  标签:教育资讯
标签:教育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