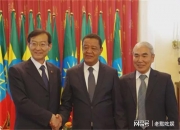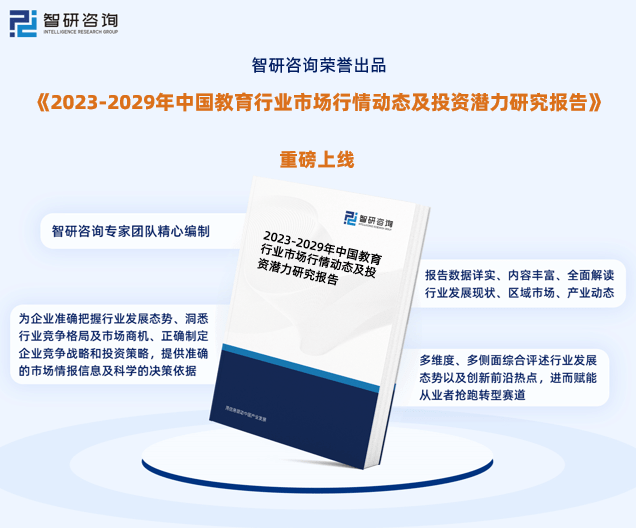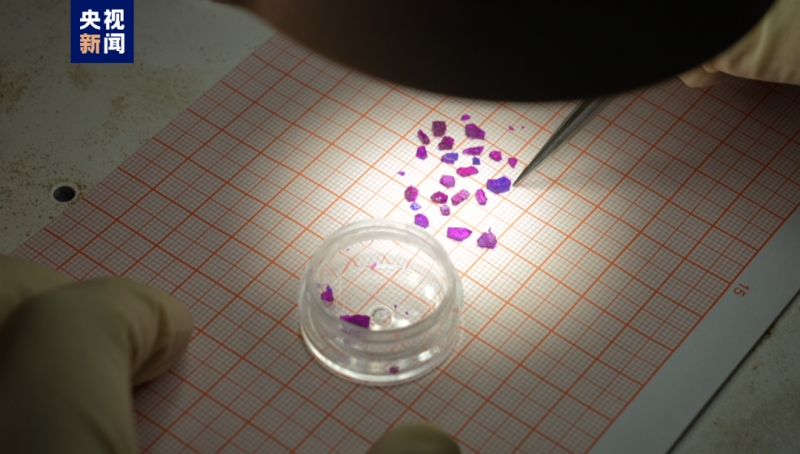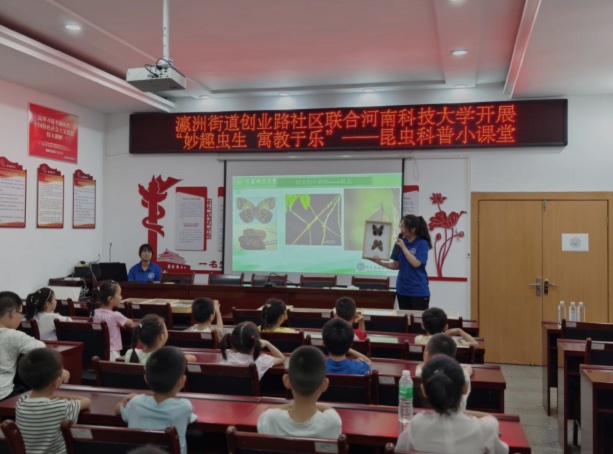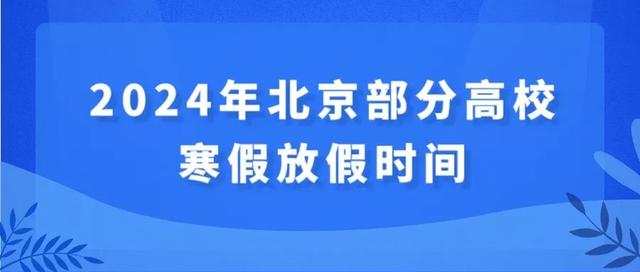从黑人当前的处境来看,对“教育公平”(更准确而言,教育中的社会正义)的狭义理解,即仅将其理解为教育机会均等,显然是偏颇、片面的。
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个梦想》演讲里说:“一百年后,黑人仍被种族隔离的镣铐和种族歧视的枷锁所禁锢。一百年后,黑人仍生活在物质充裕的海洋中一个贫穷的孤岛上。”转眼间,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黑人摘下了镣铐,但仍然戴着枷锁。“弗洛伊德之死”再次揭开了美国的伤疤,“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社会运动席卷而来。回顾民权运动的累累硕果,种族隔离被废除,表面的、制度化的种族歧视销声匿迹,黑人获得了名义上平等的投票权、教育权。然而,当这些都已经实现了,这场后民权运动还能追求什么?
华裔民权活动家陈玉平(Grace Lee)在《下一场美国革命》中描述了本应是提供均等机会的美国公立学校系统是如何进一步恶化美国黑人的处境。她认为,美国的公立学校仍然采用一种“命令与控制”的教育模式,这种模式把工薪阶层的儿童当作是流水线的产品一样无情地进行分类、测试、淘汰和认证,其目的是让他们为未来的工薪生活做好准备,成为资本主义经济机器的零件。但这种教育与黑人所面临的美国现实是格格不入的——他们在为争取权利而斗争,而美国教育却在教授顺从和屈服。随着工业自动化和制造业外流,剩下少量岗位被白人占据,即使完成这样的教育,处于社会底层的黑人仍然很难获得体面的工作。事实上,大量黑人还没完成中学教育就辍学,成为毒品经济、帮派生活和暴力犯罪的参与者,将他们所在的社区变成了战场,最终不免锒铛入狱,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监狱工业复合体”的一部分。破碎的家庭、恶劣的街区环境、帮派氛围反过来继续毒害他们下一代,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即便是少数人抓住了教育这根“救命稻草”,完成了向上流动,他们的第一想法是“逃离”,而不是“改变”。
从黑人当前的处境来看,对“教育公平”(更准确而言,教育中的社会正义)的狭义理解,即仅将其理解为教育机会均等,显然是偏颇、片面的。教育机会均等建立在“分配正义”的视角之上,其假设是如果教育资源能够被平等地分配,人们对正义的诉求就完全得到满足。但真的是这样吗?1954年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被认为是分配正义在教育领域最成功的范例。琳达·布朗一家住在堪萨斯州的托皮卡市,她每天需要花一个多小时到5 英里外的黑人学校上学。她的父亲为此向教育局申请就近入学但却遭到拒绝,原因是这所小学是专门为白人小孩设置的。在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协助下,案件被上诉到最高法院,并且学校种族隔离制度最终被宣告违宪。事实上,黑人在民权运动中获得理论上平等的教育权,一些平权法案甚至支持向黑人予以“补偿”,在大学入学和录取上予以优待,然而这并没有明显地改善他们受压迫的处境。
美国教育哲学协会前任主席肯尼斯·霍伊(Kenneth R. Howe)设想了一个思想实验:假设布朗案判决后,学校废除了种族隔离,各方面资源在所有学校中都得到了均等分配(实际上还存在很多隐性的不平等),教育机会均等就得以实现。他认为,即便是这样,教育不公仍然会以种族、阶级、性别、文化歧视和压迫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白人至上主义对黑人的压迫。这是一种更多是源自认知方式上的不公,而非分配的结果。对霍伊来说,社会正义的首要原则应该是“不压迫”,即便教育机会均等无法完全实现,社会正义仍然要求所有人获得认可和拥有自尊。从某种角度而言,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通过在线教育、教育资源数字化和虚拟现实的方式,教育机会均等在未来确实有可能得到实现,但每一个人获得了均等的份额,仍然不能等同于实现了教育中的社会正义。
这种对教育公平的本质的思考贯穿了《教育社会公平手册》,这种思考与杜威的“民主学校”、弗莱雷的“被压迫者的教育学”和阿普尔的“课程批判”遥相呼应。其基本立场是教育机会均等对实现社会正义固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将人们从压迫中解放出来。在杜威看来,“民主学校”的真谛在于创建一个“联结的空间”,让学生能够在这个空间里协作和探究,在反对不公的过程中重建知识,从而打破阶级、种族和国家疆界的屏障。弗莱雷反对当前教育体制中的储蓄式教学,这种教学将学习者视为储存信息的容器,并在师生之间建立起一种殖民统治式的关系。他主张,教师和学生应该在课堂中共享权力,通过对话式教学共同发现和建构知识,让课堂成为“民主社会组织架构的模型”。阿普尔更是直接地追问知识的合法性问题——这是谁的知识?谁来选择它?它是针对哪些特定群体?——任何课程知识都不是“纯粹的”,而是笼罩着复杂的社会权力关系,学校、课程和教育者在某种意义上都在生产和再生产不平等的意识形态,并以此维系着对社会的控制。
所有这些表述不约而同地回到了一个基本的教育议题上,即为了实现社会正义,教育应该反对说教与灌输,将学生培养成批判性的、有创造力的公共参与者,而非将他们塑造成毫无批判能力的知识接受者和消费者,或者是被剥削的劳动力和“社会齿轮”。这种批判能力能够让学生发展出更加自洽的公平观和道德感,进而在社会参与中践行公平,并追求对社会制度的变革。如批判教育学者佩皮·蕾丝缇娜(PepiLeistyna)所谈到的,“每一个人从出生之日起,就开始注定要接受特定的价值观和信念的熏陶和浸淫——这意味着融入特定的群体——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都将占据一个与生俱来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空间。但关键是他们将在学校学习何种文化实践,接受何种青年观,他们又能够对这种过程产生何种影响”。大量发展心理学的研究也表明,对公平的偏好(或者不公平厌恶)是后天习得,儿童需要内化群体的公平规则和合作规范以对抗自利动机,这恰好印证了教育在实现社会正义以及它自身的正义(即教育公平)时的重要性。
那么,教师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这里展示出一种激进的观点:教师甚至都不是赋权学生,因为声称能够将思考和表达的权力赋予他人本身是一种傲慢的行为,“对教育者而言,真正的挑战在于展现营造对话的意愿,让各种经验和世界观能够得到分享”。换言之,教师需要有能力和意愿创造自我赋权的条件,让拥有不同家庭背景和文化身份的孩子自由地探索、批判地解读,对种族主义、社会阶层和其他压迫性的结构和意识形态进行理论建构,理解经济、社会和政治现实将如何形塑他们的生活,然后创造性地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成为改变现状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和学生在权力上完全是平等,但仍然以导师、榜样和印刻者(imprinter,对儿童价值观和目标影响极大的人)引导学生,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内容知识和学科教学知识以外,教师还需要了解学生,了解他们的文化、家庭、语言和社区,并将其作为教学的资源库。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对社会正义的深层思考根植于美国的种族主义现实,脱离这种现实,我们可能就难以理解本手册向我们揭示的关于教育公平的两层含义:一是将其作为一种存在于分配范式的理想,主张教育公平是给学生提供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和进入精英阶层的向上流动的机会;二是基于批判的视角,力图引导学生在更广泛的社区中与造成社会不公的结构对抗,引领真正的社会变革。民权运动在原则上为黑人学生赢得了前者,但在择校、教育券、问责制、标准化测试等教育市场化政策和“白人大迁移”等现象的影响下,他们在现实中仍然不得不就读于实质隔离的学校。越来越多的教育者已经意识到他们需要采取另一种视角,当堂而皇之的不公平制度都被拆除以后,他们仍然需要与那些观念和认知上不公作斗争。我们看到了来自各个学科领域的案例,这些教育者通过教学来唤醒学生的批判意识,提供必要的文化和思维工具,发展其素养与能力,让年轻一代能够为改善他们所在的种族、社区和城市努力变革,而不是仅仅为了找到好工作、独善其身。
当然,这不只是一个关于黑人的故事,而是关于各种不同的群体为教育公平与社会正义奋斗的缩影。如马丁·路德·金所说,“我们将来也不满足,除非正义和公正犹如江海之波涛,汹涌澎湃,滚滚而来”。
(作者:伍绍杨、邓莉,系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和助理研究员)








 当前位置:
当前位置: 来源:互联网转载
来源:互联网转载  作者:版权所有者
作者:版权所有者  时间:2020-07-16 12:00:00 发布
时间:2020-07-16 12:00:00 发布  标签:教育资讯
标签:教育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