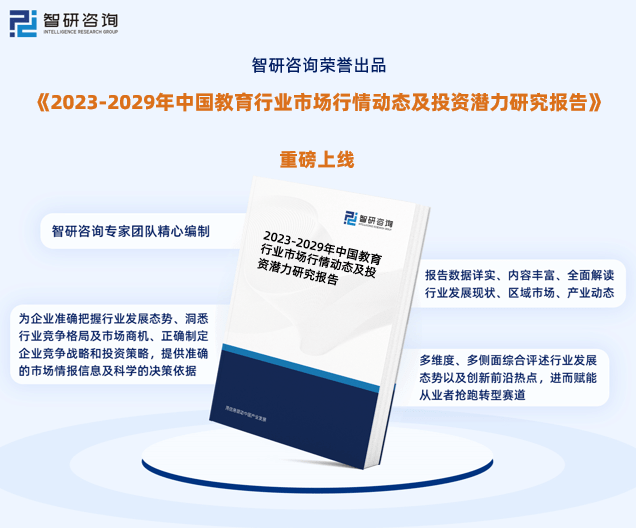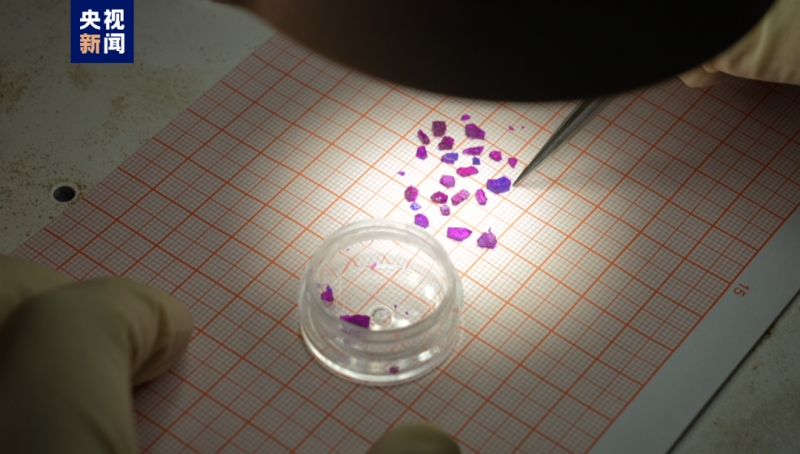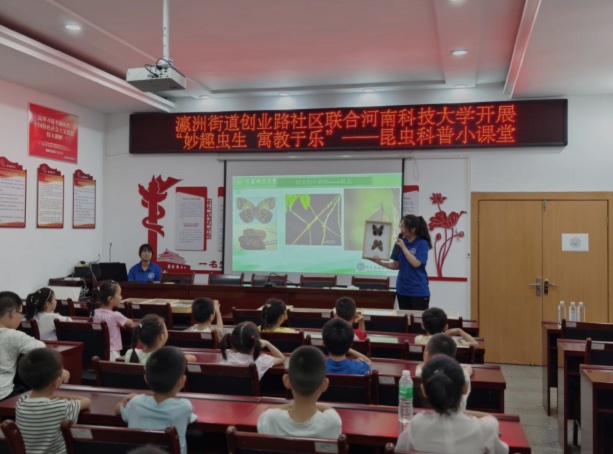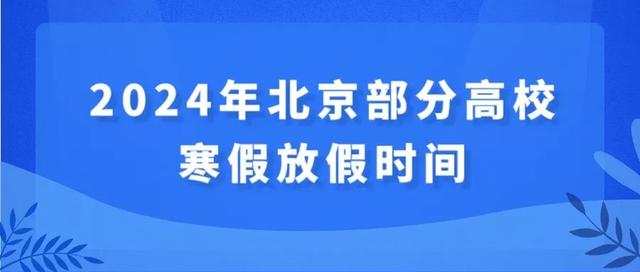14年,1048个科技小院遍布全国31个省份,覆盖83 1%的农业行业产业体系。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锁讲述—— 科技小院为什么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锁和中国农业大学200多名师生过着一种与大部分高校师生不一样的生活。他们离开北京、离开校园,长久地居住在云南、河北、内蒙古等地的村庄里。去年,在云南大理古生村,张福锁的驻村时间超过了280天。...
14年,1048个科技小院遍布全国31个省份,覆盖83.1%的农业行业产业体系。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锁讲述——
科技小院为什么行?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锁和中国农业大学200多名师生过着一种与大部分高校师生不一样的生活。他们离开北京、离开校园,长久地居住在云南、河北、内蒙古等地的村庄里。去年,在云南大理古生村,张福锁的驻村时间超过了280天。
作为一名从陕西农村长大的科学家,40多年来,张福锁看到农业领域科研与生产需求脱节、科技人员与农民脱节、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这三个突出问题。他说:“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大学就成了象牙塔,科技、人才也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2009年,张福锁和团队在河北省曲周县建立起了第一个科技小院,探索一种科技创新、社会服务和人才培养“三位一体”的新模式,推动教书与育人、田间与课堂、理论与实践、科研与推广、创新与服务更紧密地结合。
走在第15个年头,这一点星火已经燎原。
如今,全国已建立1048个科技小院,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涉及222种农产品,覆盖国民经济农业行业中农林牧渔业的59个产业体系,占比83.1%。2020年以来,科技小院模式7次写入中办、国办与科技部、农业农村部等重要文件。2022年教育部等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支持建设一批科技小院的通知》,支持全国31个省份的68个培养单位建设780个科技小院。同时,科技小院模式也得到联合国粮农组织推介,已推广到老挝和非洲8国。
科技小院缘何诞生、如何发展,又带来了怎样的改变?今年3月,在云南大理,中国教育报记者对张福锁院士进行了采访。
以下,是张福锁院士的口述。
科技小院学生学习农机使用。资料图片
“团队一年能发100多篇英文论文,但咱们父老乡亲谁读英文”
科技小院是我们2009年在河北曲周开始尝试的,最初的想法是下去看看我们的研究有没有用。
2008年,我的团队每年能发100多篇英文论文,也就是平均一个人一年有5篇论文发表,这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已经非常大。但也是这一年,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村里的父老乡亲谁读英文?我们发了这么多文章,只是给国家争了点儿光,但老百姓没用上。我提出,能不能下去,看看怎么把我们的研究用起来。
结果没人愿意去。有人和我说,张老师,我这好不容易才从农村进了北京,这不是又把我“发配”到农村了吗?当时,城镇化速度很快,都在往城里走,我们相当于要逆流而行。后来,我师兄李晓林说,他愿意下去。他是研究微生物的,完全搞的是微观研究,本来应该是做实验室研究的,而且做得也很好,既是全国优秀教师,又是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结果他说他愿意下去。李晓林是我们的大师兄,他这么一说,大家都愿意下了。
但是一下去,我们发现跟老百姓的时间凑不上。当时,我们住在实验站里,等吃完早饭8点“上班”时,地里看不见老百姓。我们问他们怎么不下地,老百姓说太阳没出来时才下地,太阳一高就回家了。我们一商量,说干脆住到村里去。
李晓林老师酒精过敏,平时一口酒都不喝。到了村里,书记逗他,说只要把两杯白酒喝了,就把一个院子免费给我们住,结果李老师真的给喝完了。我们就这么住了进去了,这一住发现效果特别好。因为你在老百姓中间了,完全是零距离。老百姓有什么事随时都找你,早上在地里看着叶子被虫子咬了,他就摘一片叶子回来,把我们从被窝里叫起来,问这是怎么回事。晚上没事,他们也跑到院子里聊天。我们那个小院后来成了村里面的活动中心。老百姓说,你们搞科技,把科技带到农家了,就叫科技小院行不行。我说太好了,这太接地气了。我们几个人就一起给科技小院下了个定义,是在农村生产一线的,集科技创新、社会服务、人才培养于一体的创新平台。
中国90%多的农民都是小农户,我们要了解小农户是怎么种地的,要怎么帮他,所以第一个科技小院建在了曲周。曲周当地都是小农户、小地块,没有规模化的经营。后来,我们把科技小院带到了吉林梨树县,这里就有专职种地的专业农民了,每家地都不小。后来,又到了黑龙江建三江的国营农场,这里规模更大,去地里用腿根本走不了,都得开着拖拉机,机械化程度很高。
这些都是我们第一批1.0版本的科技小院。我们基本就把粮食生产问题都覆盖解决了。14年后回过头看这个事,发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并不像我们设想的那么快,梨树的合作社到现在仍然是有大有小,建三江的国营农场至今全国也没有几个能模仿建成。
但经过14年的研究,对比这三个地方的种植情况,我们发现,国营农场的产量水平要比一般的小农户高30%,合作社的要低于国营农场,但又比小农户高20%左右。分析这里面的差异,关键在于技术的到位率。
科技小院举办油菜花文化旅游节。资料图片
“关键的是技术到位率,所以知识的传播、实践的示范很重要”
刚到曲周,我们做了个调查,当地9万多个小农户,10项小麦、玉米的生产关键技术到位率只有18%。这背后有缺少机械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农民不了解,知晓率低。也就是有好的技术,但是农民不知道,也用不上。
在14年的实践中,我们发现,对小农户来说,最关键的是技术到位率,对农场企业而言,最关键的是技术的创新。
因此,对科技小院而言,培训工作就很重要,知识的传播、实践的示范就很重要。在曲周,科技小院花了4年的时间,把9万多个农户的技术到位率提高到了50%。尽管这个数字还不是很高,但这9万多个农户在曲周都已经是高产户了,如果技术到位率提高到80%,他们就都是中国最好的农民。
有一年,我们在河北的一个县里做实验推广。我们把“先玉335”这个玉米品种引了进去,带着技术和当地农民一起干。当时这个县的县长是其他单位调来的,对农业不了解,也没有热情。我和他聊这个实验推广很重要,他就和我谈招商引资,把话题带远,不接我的茬儿。我们一直没有说服他。
结果玉米快成熟时,他不知怎么地跑到乡镇去了,在地头,老百姓把他拉住了,掰下玉米棒子和他讲:“我自己的玉米棒子芯很粗、种子短,人家科技小院玉米棒子的芯很细、种子长,产量肯定高。”县长很感动,当场就给我打了电话。第二天,就开了全县的现场会,把农民讲的这个棒子芯粗细的故事又讲了一遍。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产量怎么样,但会上就要求每个乡镇要搞一个百亩的示范方,在全县推广。4年后,这个县全县的产量提高了30%,农民因为小麦玉米增收能多赚3亿多元。这个县后来成了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
事实上,农技推广我们搞了那么多年,为什么搞不好?关键还是能否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科技小院就是这么做的。前几年,我跟北京大学黄季焜教授做过一个研究,如果给老百姓讲两个小时,老百姓只能接受10%的知识,过上一年就忘干净了。如果既给老百姓讲课,还跟着去地里操作,老百姓可以接受百分之四五十的知识。如果跟着老百姓干一个季节,老百姓就全学会了,并且5年以后再去回访,这些老百姓还能与时俱进地把新技术和原来学的技术结合起来,创新性地用在生产体系里面。我们这个文章也发表了,都是定量化的数据。
后来,我们从粮食作物转到经济作物,小院进入服务产业的2.0版本。因为收益高,老百姓、企业的热情很高,很愿意跟着我们学技术。现在科技小院覆盖了59个产业体系,222种农产品品类,你想吃什么我们都有,而且品质都是最好的。从2021年开始,我们在大理的古生村科技小院做的是乡村振兴3.0版。在这儿,我们希望小院不仅带来单方面的技术,还要带动全区域、更多主体参与进来,带来整个区域的人、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全面改变。
我经常说,科技小院的核心是“扎下去”。你不下去,一切都等于“0”,下去了以后人就变了,事就能做成。原来你觉得学校学的、做的那些东西没多大用处,但下去以后发现啥都有用,能给农民解决很多问题,农民也很尊重你。我们经常说,师生下去后,农民接受不接受你的第一件事,就是下去多长时间,老百姓能请你吃饭,这也是我们衡量小院学生的一个标准。
“一定要让学生吃苦,一定要让他了解真实的世界”
实际上把学生放到农村后,他们的第一反应是这“烂地方”,怎么在这生活,会想要逃跑,但是他又不能逃。所以斗争之后,学生开始学着克服困难,干很多在家里和学校不会干的事,比如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还要学着和农民打交道,让农民信任、喜欢,不然你这工作没法干。慢慢地,学生学会了表达,学会了跟人打交道,尤其是训练了自己的吃苦能力和精神。
科技小院的研究生驻扎农村两个月左右,就会发生明显变化,眼睛开始发光了,说话也充满自信。我跟李晓林老师说,这太神奇了,没想到在这么困难的地方,反而教好学生了。从那儿我们总结出,不能给学生太好的条件,一定要让他吃苦,一定要让他了解真实的世界。
农民是高看大学生一眼的,村里面的人一看你是大学生,什么问题都来找你,家里电器坏了也叫你修。我们小院的学生有个规矩,不能和农民说“我不会”,真解决不了的问题也要回复“我给你想办法”,再回来上网查资料或者找老师,最后要拿出一招来。至于这一招管用不管用,那问题都不大,只要你跟农民的互动每次都有反馈,农民就会觉得你真能干、真贴心,至于你解决多少问题,他可能倒不在乎。所以,我们的学生经常受到老乡的鼓励。14年来,还没有出现过来了小院但没转变的学生,最多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在科技小院,学生也是天天要向老百姓学习的。在科技小院,学生刚下来首先要花20多天做全村调研,家里种什么,多少投入,怎么种的,产量多少,收益多少。这些调研问题能帮你了解农民的技术、家里的情况,更重要的是,等你一户一户地调研后,就能掌握这个村的“能人”是谁,就知道村里谁有威信,谁种地种得好,谁是村里的“村霸”。
有些地方种芒果,但我们很多学生都没见过、没吃过,这怎么指导农民?我们的招也很简单,就让学生跟着20个能干的农民去看、去问,把他们的方法记下来,再一平均,就成了学生自己的做法。然后,学生再对这些做法提几个“为什么”,再加点儿自己学过的知识。最后,这个优化过的方案肯定比这20个“能人”的平均水平更高一步。到第二阶段,学生就可以跟农民“打擂台”了,看谁种得好。第一季赢不了,第二季学生肯定干得比农民好。这就给学生很大的自信了,只一两年就成厉害的把式汉了。
张福锁院士(中)与团队查看洱海水稻试验田苗情。资料图片
然后,我们要求学生做农民培训,这是小院学生最好的成长方式。我们的学生第一次给村民培训,100页幻灯片只讲了20分钟。最后下来问他讲的啥,学生说不知道,腿都在发抖。这是很正常的。等讲上几次,学生就能把20张幻灯片讲上两个小时,差不多一年多就能完成这个转变。
小院给了我们老师一个思考,那就是大学教育的失败在于,我们把什么都给学生弄得很好,连答案都想直接告诉他,结果把锻炼的机会全给弄没了,学生反倒成长不起来。把苗子扔到角落上没怎么照料,结果最后长成参天大树了,反而是天天浇水会把苗子淹死,这就是教育的规律。
有一年香港浸会大学成立了农学专业,招了15个人。他们邀请我做人才培养的经验分享,我就讲了小院的故事。当时,一个老教授就举手了,说:“张教授,我带了一辈子学生,我怎么感觉你的硕士生比我的博士生还厉害。”
后来我想,不是我的硕士生比你的博士生厉害,是我的科技小院这个平台比你的实验室厉害,因为在村里,学生既可以向农民学习,也可以向企业的技术人员学习,还能向老师学习,很快就会是个“万金油”。学生在这里掌握的都是实战经验,是综合知识,不那么单一,能解决问题。
我经常说,在学生悟之前,你给他教的东西都是没用的,灌不进去的。悟了以后,再锻炼的能力是他自己想锻炼的能力,也才是真能力、真本事。小院的学生半年到一年就能悟,这是我们小院最有价值的地方。
“通过小院改变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的方式,这是我一个大的理想”
小院也改变了我们做科研创新的模式。我们学会了在生产一线、在产业需求里面来做有用的研究。小院做的工作已经在《自然》上发表了几篇文章了,这太不容易了,如果只在实验室是不一定能做出来的。前面我提过,在曲周,我们带着老百姓做了四五年的技术培训,把技术到位率很大提高了,我们把这个实践写成文章发在了《自然》上,被作为全球样板和典型,供大家学习。
现在,我们又要在洱海做一个绿色发展的典型。从全球来看,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还要大幅度地发展,但是资源不能再被浪费,环境不能再被污染。中国正处在绿色转型的关键时期,如果我们能在农业产量进一步提升的同时,减少了投入、污染,那我们就是全世界绿色发展里最好的样板。中国经验对非洲、东南亚甚至发达国家会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所以我们的科技创新一定要进入产业,要进入主战场,你在那儿会有用不完的劲儿、会不断地去创新,不像你在实验室里做了半天,自己也不知道有没有突破,然后越做越没信心。在主战场上,生产实践会天天给你提各种问题,并且对于你的任何尝试和突破,它都会激励你、鼓励你。
我们中国在农业增产技术创新这一方面,做得很好,但现在需要把这些创新真正地带到产业里面去,形成一个系统的解决方案,全产业链地推进我们国家农业的发展、推动农民生产主体能力的提升,最终真正地让我们的生产能力成为看家本事,而不是在单方面做得很好或者文章发得很好,结果我们的产业还落后于人家,或者有些关键地方还受制于人,这就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了。
这些问题我觉得都是科技小院给我的启示。我很想通过小院改变我们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的方式,这是我一个大的理想。
但是,如何评价科技小院的学生和教师是个大问题。开始时,小院学生的开题答辩,老师们给学生的评价都不高,很多人认为没学术价值、没创新性。后来,我们向学校反映,建立起了小院学生自己的评价体系。分开之后,小院学生的表现就非常突出了。现在,学校奖学金、优秀学生评审中,我们小院学生获奖的比例非常高,因为学生既有文章,又有实际工作,还有那么多感人的故事。现在,对学生的评价已经不是问题了。
到了今天,我们还没有解决老师的评价问题。我们也常开玩笑,小院适合50岁以上的老师来做。但其实,小院也有很多的年轻教师,因为现在要“把文章写在大地上”。
过去,我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太低,追求文章数量是没办法。但不好的是,这养成了一批人想尽办法追求数量,把一篇文章拆成几篇文章发,结果“废了自己的武功”,这对他们自己和国家都是个悲哀。这个车要刹住。现在虽然在改,但是真正让大家知道去做有用的研究、做解决问题的研究、做瞄准产业创新的研究,我觉得还需要时间。我们要加大改革,否则的话,科技发展非常快,但是科技跟产业、农业科研跟农业生产实际、农业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真正的人才需求都存在脱节,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的教育急需要改革,所以我这几年搞绿色发展,想做多学科交叉、多跟产业结合,解决我们学生知识单一、不能适应社会的问题。我很想改革我们的科研模式,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学校里面读文献、做实验、发文章。但在荷兰瓦格宁根大学,除非科研人员认为自己能获诺贝尔奖,学校才会支持他做理论研究。他们认为,到产业、到生产里面,到有需求的地方去解决一个小问题,这样更有用。
14年来,我觉得科技小院已经探索出了一条科研创新、社会服务、人才培养的新路子。如果再谈更大的理想会很难,会涉及很多体系性的东西,需要很长的时间,但现在我们在小院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儿。(本报记者梁丹 采访整理)
[ 责编:邱晓琴 ]








 当前位置:
当前位置: 来源:教育信息网(转载)
来源:教育信息网(转载)  作者:版权所有者
作者:版权所有者  时间:2023-04-19 08:44:00 发布
时间:2023-04-19 08:44:00 发布  标签:新闻
标签: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