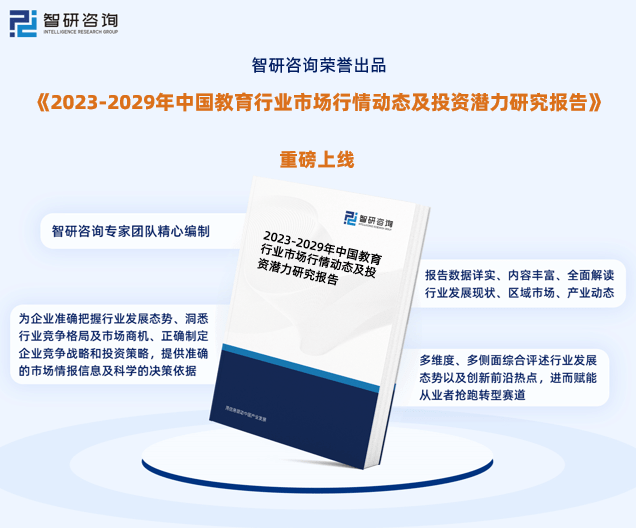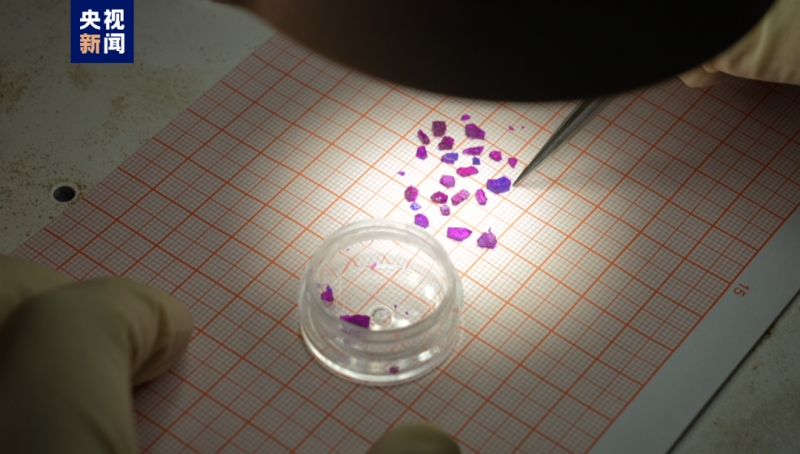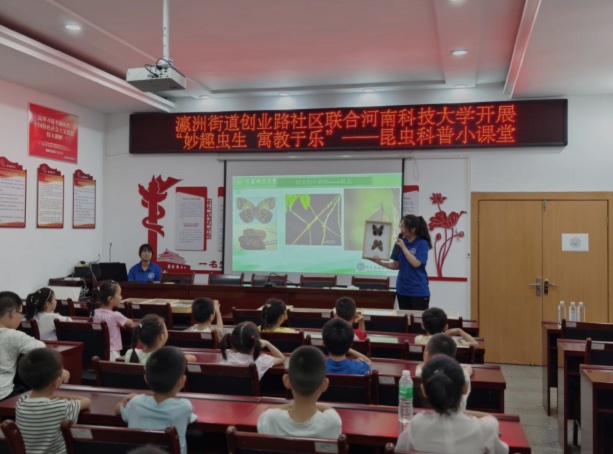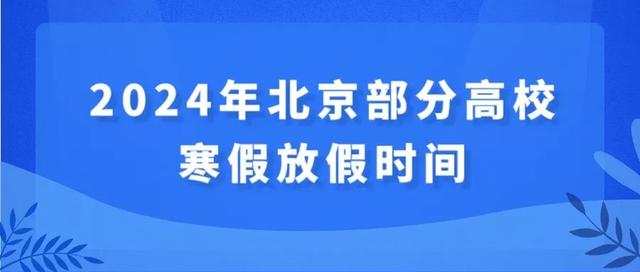进入现代以后,中国诗歌在主题向度、语言形态和构造体式等方面均出现很大变化,诗教的社会文化语境及施行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诗教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在诸如“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及“诗言志”“思无邪”等为人熟知的表述的促动下,诗歌的影响遍及从国家社稷、社会风尚到日常礼仪、个人修为的不同层面,使得诗歌在中国古代远不止于一种文类,即不仅仅是个人表情达意的方式,而且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与政治、伦理、风俗、文化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体现的正是诗教的目的和功能:一些重要思想乃至制度理念被以诗歌的独特形式进行传布与渗透,用来规训人们的言行举止、引导社会文化的路向,即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虽然有“乐”作为与诗相伴而生的手段,但中国古代诗教总体上偏于教化。
进入现代以后,中国诗歌在主题向度、语言形态和构造体式等方面均出现很大变化,诗教的社会文化语境及施行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特别是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诗教,教育观念的革新与迁移深刻影响了其理论内涵和实践指向。近代以来由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等人开创,由鲁迅、宗白华、朱光潜等人丰富完善的美育,通过引入康德、席勒等西方理论家的美学思想,确立了以情感为核心、倡导“审美无功利”、以“立人”为旨归的理论构架,提出“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蔡元培为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大辞书》撰写的《美育》条目),“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理想的教育是让天性中所有的潜蓄力量都得尽量发挥,所有的本能都得平均调和发展,以造成一个全人”(朱光潜《论美感教育》)等主张。这些美育观念从多方面推动了中国诗教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促使诗教直面现代乃至当代的处境。
依照朱光潜的“诗教就是美育”这一说法,诗教显然是现代艺术、审美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林语堂所说:“中国的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似乎应和了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说),虽然他所讲的“中国的诗”是指古典诗歌,并且中国诗歌经过现代性的洗礼之后,其样态及其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已经发生巨变,仅有百年历史的现代诗歌被认为失去了古典诗歌的辉煌和魅力,但是诗歌本身仍然具有相当的感召力,对人类的精神生活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由此,处于现代境遇中的诗教,或者说在现代美育观念影响下的诗教,实际上包含两个问题向度:一是传统诗教的适应性,即传统诗教通过调整、转换,寻求合乎现代人生存状态、审美趣味和心理需求的路径;一是根据现代诗歌的特性,找到诗歌与社会文化的连接点,探索诗教的现代意义和方式。
诚然,现代美育所倡导的以情感为核心的观念,有助于引导诗教施行过程中凸显诗歌的抒情性本质,并将诗歌理解的重心转移到对基于诗歌本体的审美能力的培育。不过,在诗教中突出诗歌的情感因素和抒情性一面,不宜忽略诗歌所应具有的智性、理趣和思辨等其他特质;而回归诗歌本体,或许一定程度上能去除传统诗教过分教化之弊,但并非要将诗歌拉回到“内部”,拘泥于单纯的语言、形式等构件,切断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在“故步自封”中慢慢失去活力、直至萎缩。有目共睹的是,在整体性逐步丧失的现代社会,知识体系一度趋于专门化、精细化,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也日益碎片化、单子化,这对诗歌的创作、接受与传播提出了巨大挑战。因此,对于现代诗教来说,除了“情”这一维度外,更应强调诗歌面对和处理纷繁变幻的社会生活的综合能力,在诗歌与社会文化之间构建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以保持诗歌自身的活力。
至于现代美育主张的“审美无功利”,显然直接因袭了康德的理论,考虑到现代美育诞生的时代背景,不难体察这一主张隐含的具体针对性。当蔡元培提出“纯粹之美育……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时,他期待的是以“无功利”之审美的“纯粹”性,消除当时“大多数之人皆汲汲于近功近利”的积患,涤荡弥漫于国人胸中的污浊之气。就此而言,不应表面地看待现代美育所倡导的“审美无功利”,而是要深入洞悉其观念指引下的实践及其效应。同样,现代诗教也曾表达过强烈的“无功利”的诉求,提倡“纯诗”、极度强调形式、技艺的自足性,以抵制长期附加于诗歌之上的种种“外在”要求。一味追求诗歌“无功利”所具有的片面性显而易见,它会导致写作者狭隘地理解“诗性思维”(维柯)的含义和价值,皮相地趋附海德格尔大力阐释的荷尔德林之“诗意地栖居”。为人所津津乐道的“诗性”“诗意”,都不是诗歌“无功利”的浅表的代名词,也不是用于装饰(甚至粉饰)生活的缀物。实际上,“诗性”显示了一种独特的创造能力,是人类与自然万物建立联系的方式;“诗意地栖居”并不表明某种独善其身、超然于尘世之外的态度,也不应被当作遁入“世外桃源”的托词。按照海德格尔的解释,“诗意是人的栖居必备的基本能力。但人之具有诗的能力,始终只需遵循如下尺度:其存在要与那本身就喜爱人,并因此需要人出场的东西相契合”。而抵达这一“尺度”的重要前提就是荷尔德林在诗中咏唱的“善”,故而“诗意地栖居”体现的是美与善的协调。在据说是荷尔德林与黑格尔、谢林共同起草的《德国唯心主义的最初纲领》一文中,就有如此论断:“理性的最高方式是审美的方式,它涵盖所有的理念。只有在美之中,真与善才会亲如姐妹。”显然受到这一观点影响的朱光潜也认为:“善与美不但不相冲突,而且到最高境界,根本是一回事,它们的必有条件同是和谐与秩序。从伦理观点看,美是一种善;从美感观点看,善也是一种美。”这正是看似“无功利”的审美的辩证属性,在现代诗歌“冲击极限”式的技艺锤炼中,也许隐含着诗学自身的伦理,通向的是一种与母语、民族记忆相关的社会文化担当。
现代美育以“立人”即塑造“完人”为最终目标,这与现代诗教的基本理念是一致的。传统诗教非常重视通过诗歌养成完美人格。在中国古代,诗歌之于“修身”绝非一般意义的怡情养性,而是全方位完善自我的绝佳途径。不过,古今诗教对“完人”有着很不一样的期许和取向,现代诗教已不可能像古代诗教那样,仅仅视以“仁”为内核、具有德性的君子为“完人”,而是对之倾注更丰厚内涵、更富于现时代特征,以回应急剧变化的历史语境。至少应该在马克思预期的“人的解放”的意义上理解现代社会的“完人”,即一种具有“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人格形象。依此目标,现代诗教对人的诲示就不限于心智上,而更在于一种将其置于“社会关系”之中所产生的创造力。
在社会文化日渐多元化的当下,倘若不是孤立、抽象、静态地领悟诞生于上世纪初的现代美育所关涉的美、审美、美感等命题,它的某些观念对诗教的拓展仍然具有启示价值。未来诗教关于诗歌的界说中,诗歌之美不再是单一的,而是立体的,不只提供赏鉴、实现“净化”,更具有海德格尔所说的超越性的“拯救的力量”,不仅能够弥合“人心”,而且将重塑人在技术时代的命运和位置。
(作者:张桃洲,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当前位置:
当前位置: 来源:教育信息网
来源:教育信息网  作者:版权所有者
作者:版权所有者  时间:2019-10-09 12:00:00 发布
时间:2019-10-09 12:00:00 发布  标签:教育资讯
标签:教育资讯